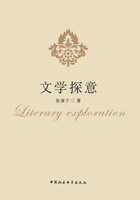
诗歌需要思想和情感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我们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可是在传统与现代之交,我们的诗歌却走向了“萎缩和低迷”,甚至有人说“诗歌已经死亡了”。这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归咎于“市场的张力和读者的阅读习惯”的,有认为是“诗歌在中国古代的隆崇地位”给今天的诗歌“埋下了暗礁”的,有怪怨一个时期以来,诗歌的“外延不加节制的膨胀”,“把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应该承担的责任安放到了它的头顶”,使“诗歌最根本的品质——抒情和审美的功能严重受创”的,还有认为当今的中青年诗人“先天性营养不良”,既“丧失了革命年代的激情”,也“拿不出起码的勇气与真诚,去探索诗歌语言新的可能性”的,等等不一而足,都不能说没有切中肯綮。但笔者坚持认为,诗歌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是诗歌的思想和情感越来越贫乏、诗歌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的实际所造成的。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当下诗歌最应该反省的重大问题。而令人忧心的是,这一点却恰恰最不被我们的诗坛所承认或接受。
要阐明这个问题,须先辨清诗歌的本质功能到底是什么。也许有人会说,这个问题不是明摆着的吗,诗歌的本质功能就是抒情和审美呀。不错,这种判断,或这种观点,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谓文学回归本位的活动之后,已经基本上被诗坛所认同了。但是诗歌抒什么样的情?审什么样的美?这个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好。在喊出文学回归本位口号的初期,诗歌和小说等其他文学一样,先是诗人们做着各式各样的所谓诗歌文本的实验和诗歌语言的探索;接着是受西方后现代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颠覆传统,解构旧体,远离生活,进行所谓人性本能的挖掘和表现;再后来是市场化的冲击,本属于精神表现的诗歌也向物质化靠拢,媚于受众,有意地追逐商业炒作和包装,直到把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生真相的诗歌传统解构殆尽、扔掉或丢光……可到头来怎样呢?“今天还有谁在读诗?”李舫女士在《谁将诗歌轻轻翻过》 一文中这句令人酸楚的发问,就是最明白不过的回答。
一文中这句令人酸楚的发问,就是最明白不过的回答。
笔者这里无意否认文学回归本位的活动,也无意否定诗人们所作的各种努力。但时至今日,我们也不能不静下心来,进行深刻的反省,我们今天的诗歌回归本位了吗?或者说眼前的状况就是诗歌的本位吗?恐怕没有谁敢肯定地来回答这个问题。能够深一层追究的是,在当初喊出回归本位的时候,我们是否认真地想过——到底什么是文学的本位?或者文学的本位就只是审美吗?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是否回到了所期望的审美本位?今天看来,审美徒剩下一副漂亮的外衣,或者只成为了一个漂亮的借口。真实的情况是,不少的诗人忽视自己思想情操的修养,自身缺乏对现实生活积极的态度和真切的体验,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真相的关注,放弃了对人类崇高精神的追求,让自我和欲望一味地膨胀。其实质正像诗人老巢所指出的,是“把目光从现实人生收回而投放到个人生命脆弱与黑暗的病态部分,孤独、绝望、灵魂漂泊”,让“这些从西方后工业社会舶来的灰色情绪弥漫于字里行间”。 难道这些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诗歌本位吗?难道这种状况还没有到值得我们认真反省的时候吗?诗人老巢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也是具有诗人的良心的,因而他疾声呼吁:“如果我们不及时反省与自救,任现在的状况延续下去,那么历史将以最轻描淡写甚至是空白的方式,把我们轻轻翻过。”
难道这些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诗歌本位吗?难道这种状况还没有到值得我们认真反省的时候吗?诗人老巢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也是具有诗人的良心的,因而他疾声呼吁:“如果我们不及时反省与自救,任现在的状况延续下去,那么历史将以最轻描淡写甚至是空白的方式,把我们轻轻翻过。” 可作为每一个有责任的当代诗人,有谁愿意让历史“把我们轻轻翻过”呢?又有谁能承担得起这被“轻轻翻过”的责任呢?
可作为每一个有责任的当代诗人,有谁愿意让历史“把我们轻轻翻过”呢?又有谁能承担得起这被“轻轻翻过”的责任呢?
需要进一步辨别的是,如何理解审美?如何看待诗歌的社会功用?审美并不只是诗歌唯一的功能。笔者还是同意李舫女士的说法,“市场不过给了文化浅陋的外壳,而我们内心真正能够景仰的浩然正气,能够救赎的光明朗照,还得由浩浩汤汤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她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对诗歌功能的最简捷、最深邃的描述。” 之所以“最简捷、最深邃”,是因为我们的先圣对诗歌本质功能的认识是最朴实的,也是最清醒、最深刻的。几千年来,大凡优秀的诗歌基本都是沿着这种认识前行并一代代传承的。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对诗歌本质功能最准确和最科学的概括,依然可以作为我们当下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同样,“诗言志,歌咏言”,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经典的意义,仍然是“诗歌开山的纲领”(朱自清),仍然需要我们当代的诗人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挖掘其中的内涵和宝藏,来为今天的诗歌服务。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复古吗?笔者不这样认为。“言志”,就是诗歌最本质的功能,“兴、观、群、怨”就是诗歌“言志”的最佳表现和最好的功效。我们不能因为过去一个时期过于强调了诗歌干预社会政治、甚或为政治服务,就因噎废食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就否定诗歌先天就有的道德功能和社会批判价值。审美是需要的,可“美”从来都是和“真”、“善”紧密相连的,脱离了“真”和“善”的“美”,也一定是毫无意义的,“真”和“善”都是审美固有的内涵。当然,审美有它的历史规定性和时代特性,但任何时代的审美都不能抛开“真”和“善”的内涵,而使审美徒具一副美的空壳。其实,“诗言志”,也并不排除诗歌的抒情和审美的功能,相反,“言志”就是抒情,“兴、观、群、怨”就是审美应具有的社会内涵。它们都是后世诗歌重视思想和情感的理论根源。我们的先圣一开始就给诗歌赋予了这样积极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这也正是数千年来,人们热爱诗歌、喜欢诗歌、离不开诗歌的重要原因。可我们为什么偏偏要抛弃这些,而去自我打压诗歌的这些最有价值的功效呢?难道我们这代诗人真的没有勇气去面对社会,面对人生,真的没有能力承担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责任吗?不错,诗的确需要独抒性灵,诗也的确需要表现人性的本质。可人既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人。诗要独抒的“性灵”,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诗要表现的人性本质,也决不能是动物性的本能。我们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空喊什么抒情和审美了;同样我们再也不能妄自菲薄地认为传统的就是落后的,经典的就是应该被解构或被颠覆的,外来的就一切都是先进的。须知先进的文化绝不是仅凭其产生的时间和地域就可以轻易判定的。我总是相信,先圣的哲思往往含纳着人类的智慧和精辟的见解,对我们后来人总是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之所以“最简捷、最深邃”,是因为我们的先圣对诗歌本质功能的认识是最朴实的,也是最清醒、最深刻的。几千年来,大凡优秀的诗歌基本都是沿着这种认识前行并一代代传承的。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对诗歌本质功能最准确和最科学的概括,依然可以作为我们当下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同样,“诗言志,歌咏言”,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经典的意义,仍然是“诗歌开山的纲领”(朱自清),仍然需要我们当代的诗人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挖掘其中的内涵和宝藏,来为今天的诗歌服务。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复古吗?笔者不这样认为。“言志”,就是诗歌最本质的功能,“兴、观、群、怨”就是诗歌“言志”的最佳表现和最好的功效。我们不能因为过去一个时期过于强调了诗歌干预社会政治、甚或为政治服务,就因噎废食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就否定诗歌先天就有的道德功能和社会批判价值。审美是需要的,可“美”从来都是和“真”、“善”紧密相连的,脱离了“真”和“善”的“美”,也一定是毫无意义的,“真”和“善”都是审美固有的内涵。当然,审美有它的历史规定性和时代特性,但任何时代的审美都不能抛开“真”和“善”的内涵,而使审美徒具一副美的空壳。其实,“诗言志”,也并不排除诗歌的抒情和审美的功能,相反,“言志”就是抒情,“兴、观、群、怨”就是审美应具有的社会内涵。它们都是后世诗歌重视思想和情感的理论根源。我们的先圣一开始就给诗歌赋予了这样积极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这也正是数千年来,人们热爱诗歌、喜欢诗歌、离不开诗歌的重要原因。可我们为什么偏偏要抛弃这些,而去自我打压诗歌的这些最有价值的功效呢?难道我们这代诗人真的没有勇气去面对社会,面对人生,真的没有能力承担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责任吗?不错,诗的确需要独抒性灵,诗也的确需要表现人性的本质。可人既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人。诗要独抒的“性灵”,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诗要表现的人性本质,也决不能是动物性的本能。我们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空喊什么抒情和审美了;同样我们再也不能妄自菲薄地认为传统的就是落后的,经典的就是应该被解构或被颠覆的,外来的就一切都是先进的。须知先进的文化绝不是仅凭其产生的时间和地域就可以轻易判定的。我总是相信,先圣的哲思往往含纳着人类的智慧和精辟的见解,对我们后来人总是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笔者非常赞赏诗人老巢的断语:“再出色的诗人也不能脱离时代走到命运的外面写出伟大的作品。” 新时代的诗歌,不仅需要形式或文本的探索和革新,更要有思想和情感的力量作支撑。而鲜活的思想和动人的情感,只能来自诗人对现实生活的亲身体验和真实感悟,来自诗人对现实生活诗意的解读和理想化的改造,来自诗人对生活的意义的深刻洞察和悉心提炼。这些道理,早已经被我国诗歌发展的优良传统所证明了的。相反,一个诗人不懂得什么是生活的意义,一味地让内心充满了“自我和欲望”,甚或是“孤独和绝望”,那么他就不可能走进现实的生活,就不可能获得鲜活的思想和情感,他的创作就不能走出狭小的圈子,只能徘徊甚或停留在思想和情感贫乏的歧途,他的诗歌就不可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果那样,我们的诗歌还怎样走出当下的困境?
新时代的诗歌,不仅需要形式或文本的探索和革新,更要有思想和情感的力量作支撑。而鲜活的思想和动人的情感,只能来自诗人对现实生活的亲身体验和真实感悟,来自诗人对现实生活诗意的解读和理想化的改造,来自诗人对生活的意义的深刻洞察和悉心提炼。这些道理,早已经被我国诗歌发展的优良传统所证明了的。相反,一个诗人不懂得什么是生活的意义,一味地让内心充满了“自我和欲望”,甚或是“孤独和绝望”,那么他就不可能走进现实的生活,就不可能获得鲜活的思想和情感,他的创作就不能走出狭小的圈子,只能徘徊甚或停留在思想和情感贫乏的歧途,他的诗歌就不可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果那样,我们的诗歌还怎样走出当下的困境?
2006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