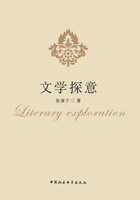
文学不能没有崇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一些作家一味追求所谓的“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文学越来越缺少对生活中的崇高美的描写,坠入了一种期望让平民心绪得到最低层次满足的平庸情趣之中。追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对人们长期的禁锢被打破了,人们再也不相信过去那种假大空和伪崇高了,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转型,人们的价值目标发生了变化,追求物质享受,讲究实惠的生活,成为人们的普遍心态。这两方面的原因影响到文学,似乎只有写实主义才能适应和表现眼前的生活。
问题在于,写实主义就可以不要崇高了吗?或者说写实主义的文学就不能表现崇高了吗?
不难看出,写实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把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生存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可是这些在社会底层生活的人,难道他们就没有崇高可言吗?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而那些普通人、平民、小人物不正是人民的一份子吗?看来关键还在于我们怎样认识这些普通人、平民、小人物,怎样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还有就是我们怎样理解崇高。也许过去那一套假大空式的伪崇高把人们欺骗怕了,让人们普遍对崇高有了一种畏惧感和神秘感。其实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今天,我们对崇高的理解应该宽泛化。我们反对伪崇高,或者说崇高不能虚伪化。但崇高也并不神秘,崇高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每个公民都应该学习甚至具有的一种美好的品质。崇高不一定都是伟大人物才有的,普通人或小人物也有平民式的崇高,而这种平民式的崇高更显亲切,更真实,更容易感受得到。中央电视台前段时间播放的电视剧《大姐》,描写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观看之后,我们不由对主人公“大姐”产生一种崇敬的心理,觉得她的身上就有崇高的品质,她的形象就是崇高的。
这样来理解崇高,有人也许会说,这不是降低了崇高的价值和意义了么?我们不这样认为。过去,我们总是以为只有英雄人物或伟大人物才会具有崇高的品质和精神;其实,崇高也存在于社会底层的人身上。郎加纳斯说过:“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论崇高》)。 心灵的伟大与否,决不是以人的身份为标准的。鲁迅当年描写的人力车夫,与那个只为个人生计着想,一味埋怨人力车夫多管闲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比,人力车夫的心灵不是更伟大吗?所以鲁迅先生在作品中极力赞扬人力车夫:“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一件小事》)鲁迅在那个年代这样来赞扬人力车夫,可见其眼光之高。同时也给我们怎样认识崇高和怎样表现崇高树立了标准和典范。
心灵的伟大与否,决不是以人的身份为标准的。鲁迅当年描写的人力车夫,与那个只为个人生计着想,一味埋怨人力车夫多管闲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比,人力车夫的心灵不是更伟大吗?所以鲁迅先生在作品中极力赞扬人力车夫:“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一件小事》)鲁迅在那个年代这样来赞扬人力车夫,可见其眼光之高。同时也给我们怎样认识崇高和怎样表现崇高树立了标准和典范。
不可否认,崇高往往与英雄主义相联系。时代需要英雄,但崇高不一定都是英雄式的表现。生活中,崇高又往往和牺牲精神相联系,而富有牺牲精神的不仅仅只有英雄,普通人或小人物也有牺牲精神,只不过常常不被人们注意罢了。事实上,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几十个民族的大国,没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奉献和牺牲,我们的国家就很难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也很难有今天这样巨大的变化。因此,文学应该关注和描写这些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生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但同时,更应该发现和挖掘他们身上的一切优秀的品质,包括崇高的品质。
崇高的品质是和龌龊相对立的。龌龊的东西,往往是一个民族身上的劣根性的表现,是要被批判和被抛弃的。崇高也是与平庸格格不入的,平庸是一个人软弱和无能的表现,它让人萎缩,缺乏阳刚之气,让人丧失信念、勇气和前进的力量。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不追求崇高精神,这个民族或国家就不会进步,就没有希望;一个集体或一个人,不追求崇高的品质,就会意志消沉,缺乏朝气,就会变得庸俗,贪图享乐,甚至唯利是图,严重者还会陷入贪婪、卑鄙、无耻和道德败坏的境地。应该认识到,世俗化的倾向给文学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是崇高精神的缺失。这显然是与我们今天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相背离的。社会越进步,越文明,崇高的品质就应该更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崇高是人类精神中应有的品质,也是文学应具有的品质。崇高在生活中。表现崇高是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