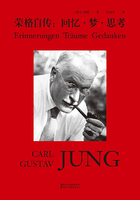
第6章 中小学时光(3)
家母的家族里有六名牧师,家父的家族中,不仅家父、他两个兄弟也是牧师。所以,我听到过很多有关宗教的谈话、神学讨论和布道。我总感觉:“是,是,这很好。可那秘密如何呢?它的确也是圣宠的秘密。你们一无所知。你们不知道,上帝愿意我甚至行不公之事、想该死之事,以体验他的恩宠。”他人所说一切皆隔靴搔痒。我想:“上帝啊,想必还是有人会略知一二,真相总还会在某处。”我在家父的藏书中翻腾,只要关于上帝、三位一体、精神、意识,就找出来读,囫囵吞枣,不甚了了,不禁一再想:“他们也不知道!”我也读了父亲的《路德圣经》。不幸的是,通常对《约伯记》所做“使人虔敬的”解释使我无心深入。否则我会找到慰藉,也就是第九章第三十节如下,“若我即刻以雪水自涤……,则汝将溺我于溷秽”。
家母后来告知,我那时常常抑郁,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我专心于秘密。坐于那块石上就是至福的宁静,它让人疑惑尽消。一想到我是石,就不再纠结,心想,“石头没有不安,没有要说与人听的冲动,恒久不变,长存成千上万年。自己则只是过眼云烟,化为千情万绪,如倏然炎上,继之熄灭”。我是自己情绪的集成体,而我身上的一个他者是无始无终的石头。
二
那时还会深刻怀疑家父所言一切。一听到他宣讲圣宠,我总是想到自己的经历。他所言之事听上去空洞乏味,犹如一人讲述自己将信将疑或者只是道听途说的故事。我想帮他,可不知以何方式。羞怯也阻止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或者干涉他的先入之见。对此,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太小,另一方面担心唤起“第二人格”的那种权威感发挥作用。
后来,我十八岁时,与家父讨论颇多,总是暗自希望让他知晓造就奇迹的圣宠,借此在他心中纠结时施以援手。我深信,若他让上帝遂意,一切均会好转。我们的讨论结局却始终难如人意。它们激怒他,让他郁郁寡欢。他往往说道,“嗐,说什么呢。你总想思考,不该思考,而应信仰”。我想:不,得体验、获知,说的却是“给我这种信仰”,他每次都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转过身去。
我开始交友,大多与家世平常的害羞小伙子。我的成绩有了改观,随后几年里,甚至独占鳌头,却发现后面有人嫉妒,一有机会就想超越我,这让人败兴。我憎恶一切竞争,若有人把游戏变成角逐,自己就退出。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位居第二,这让人舒服多了。学校作业真够讨厌的,自己不想还因争强好胜而让它碍手碍脚。我感念特别信赖我的少数几个教师,尤其愿意缅怀拉丁文教师。他是大学教授,睿智之人。因为家父教过我,我六岁就懂拉丁文。所以,我的老师经常打发我去大学图书馆,在做练习时给他取书,于是,我尽量延时返回,归途上入迷地翻看。
多数老师认为我既愚蠢又狡黠,学校里出了什么岔子,先怀疑我。某处干仗,就猜我是挑唆者。其实,我只有一次卷入打斗,发现一帮同学心怀敌意,他们七个人设伏突袭我。那时我十五岁,已经又壮又高,脾气火暴。我火冒三丈,抓住一个人的双臂,把他甩起来,借他的腿打倒了边上几个。老师们知道了此事,但我只隐约记得打了官司,觉得不公。从那时起却清静了,没人再敢碰我。
我有敌手,人家多半无端冤枉我。虽然出乎意料,但要说起来并非不可理解。所有指责之辞激怒了我,但自己无法否认这些。我对自己知之甚少,而少许所知之事充满矛盾,使自己不可能问心无愧地驳斥任何一项责备。本来总是良心不安,意识到自己现在有罪过,可能有罪错。所以,我对指责尤为敏感,因为它们多少有些一语中的,即使我没有真做什么,也还可能干得出来。有时,我甚至做不在现场的记录,以防遭控拆。我要真做了什么,还觉得轻松了。那样,我至少知道何处亏心了。
当然,我用外在的自信补偿内心的不自信,或者确切地说,未经同意,缺陷即自我补偿了。我却发现自己是有罪而又想无罪者,心底始终知道,自己是双面人,一个是父母之子,上学,悟性不高,专心、勤奋、正派、整洁,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另一个则成年,甚至年老、多疑,谁也不信,远离人世,但面对自然、土地、太阳、月亮、天气、生物,尤其面对夜、梦和“上帝”在我身上直接造成的一切。此处,我给“上帝”加了引号,因为觉得自然与本人一样遭上帝废弃,作为非上帝,虽则由他创造用于表示其自身。我怎么都想不通,一模一样为何只应涉及人。我觉得,不错,崇山峻岭、江河湖泽、华林秀树、秾芳秀华、美禽妙兽对上帝神灵的说明远胜于衣着可笑、庸俗、愚蠢、虚荣、谎话连篇、自恋烦人的人。所有这些特性,我可是太有切身体验了,亦即从那种头号人格中,从1890年的学童身上。不过,还有一个领域,有如一座庙,每个踏足者皆发生改变,因观察全世界而倾倒,加之出神忘我,他只能称奇、赞叹。此处生活着“他者”,了解上帝是隐蔽的、个人的而又超个人的秘密。此处没有什么把人与上帝分隔。对,似乎人的精神与上帝同时展望万物。
我如今用句子展叙之事,当时却并非清晰自觉,但可能预感强烈,感受深切,独处时就可能进入这种状态,此时,自知有尊严,是本真者,因而寻求不受干扰,寻求他者、二号人格独处。
终我一生,头号与二号人格相反相成,与通常医学意义上的“分裂”无关,相反,它们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宗教,向来对人的二号人格、对“内心的人”指手画脚。我一生都是老二扮演主角,而我始终尝试让由衷之事信马由缰。老二是个典型形象,但自觉的领会通常不足以看出人亦如此。
教堂渐成烦恼之地,因为那里众声喧哗,(我都想说:无耻)宣扬上帝,说他意欲何为,所行何事,告诫人们要有哪些情感,要相信哪种秘密,但我知道,它是最为内在、由衷、无以言状的确信。我只能由此推断,看来无人知晓此秘密,连牧师也不知;否则他们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泄露上帝的秘密,用乏味的伤感言辞亵渎难以言喻的情感。此外,我肯定,若要接近上帝,这是背道而驰,因为我可是有切身体会,这种圣宠只给予无条件让上帝遂心者。此事虽也得到宣扬,但始终附带的前提是,上帝的意志通过天启为人所知,我则觉得它是最不为人知之事,似乎人人其实日日不得不研究上帝的意志。我虽不做此事,但肯定,一旦迫在眉睫,就会这么做。头号人格过频、过多地占用我的精力,似乎有人甚至用教规代替可能出人意料、令人吃惊的上帝意志,而且旨在不必领会上帝的意志。我疑心日重,觉得家父与其他牧师的布道难堪。周围所有人好像都觉得隐语和散发出来的浓重暧昧意味是理所当然的,对一切矛盾都不假思索地忍气吞声,如上帝全知,当然预见到人类历史。他创造人,使他们必得犯罪作孽,而尽管如此,他还是禁止罪恶,甚至罚以永远打入烈火熊熊的地狱。
在我的思考中,魔鬼长期不起作用,令人觉得它是豪强的看家恶狗。只有上帝对世界负有责任,我可是太知道了,他也很可怕。家父充满感情地布道,称颂并恳求“亲爱的上帝”、上帝爱人、人爱上帝,我愈益觉得可疑、毛骨悚然。疑心又起:他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他可能让人把我——他儿子像以撒一样作为人祭加以宰杀,或者交给不公法庭让人把他儿子像基督一样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不,他做不到。那他也许不可能满足上帝的意志,《圣经》自身显示,上帝的意志可能绝对可怕。如果还有人告诫过,要听从上帝胜于听从人,我明白这话只是随口说说,有口无心。人们显然完全不了解上帝的意志,否则纯粹出于敬畏上帝,就会诚惶诚恐地处理这个中心问题,上帝可以游刃有余地在无助者身上贯彻他那惊人的意志,我就遭遇过。佯言了解上帝意志者可能预见到他促发我做了什么吗?无论如何,《新约》中此类人毫无踪迹。《旧约》,尤其是《约伯书》本有可能在这方面给我启悟,那时我还是太不了解这点了,即使在所上的坚信礼课程中,也未听说类似之事。当然提及敬畏上帝,被视为不合时宜,算作“犹太式的”,早就为基督教爱的福音和上帝的善良所超越。
童年经历的象征意味和图景的残暴性让我极为忐忑不安,自问:“究竟谁如此说话?谁恬不知耻,如此赤祼祼而且在庙中展示阳具?谁令我认为上帝如此可鄙地摧毁他的教堂?这是魔鬼安排的?”我从未怀疑正是上帝或者魔鬼如此言说或者如此行事,因为我确切感觉到,不是自己想出这些念头和图景。
这些是我平生的关键事件,当时茅塞顿开,自己有责任,命运走势系于自身。我面临必须回应的问题,谁提出此问题呢?无人作答。我知道,自己会发自肺腑地回答:我独自面对上帝,而只有上帝问我这些可怕之事。从一开始,我心里就有无可比拟的命定感,似乎把自己置于须过完的一生中。内心有自己从未能证明的安定,但它在我面前得到了证明。我从未有过安定,但它有我,常常与确信之事相反。无人能妨碍我坚信,自己注定做上帝所愿之事而非我愿之事。这经常让我感觉在一切关键事物上并非与人共处,而仅与上帝同在。每当我在“彼岸”,不再孤单,就游离于时间之外,我在千百年间,而作答者已经长存而且永存。与那个“他者”的谈话是我最深刻的经历,一面浴血奋战,一面心醉神迷。
我当然不能与人谈论这些事,除了可能与家母推心置腹,周遭无人可倾诉。她好像与我想法相似,但我很快发觉,跟她谈话不过瘾,她对我特别欣赏,而这不是好事。所以,我依旧独自思考,也最好如此,独自嬉戏,一人漫步、梦想,有别无他人的神秘世界。
对我而言,家母是良母,古道热肠,平易近人,富态毕现。她对大家都侧耳细听;也爱谈天说地,口若悬河。她在文学上天赋异禀,品位独标高格,渊然深识,但无处得到恰当的表现;依旧隐藏在一个确实可爱、肥胖的老妇背后。她相当好客,厨艺出色,极富幽默感。可能有的因循守旧观点她都有,但另一方面,她身上也出现潜意识的人格,威力出乎意料,一个不显山露水的大人物,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这点毫无疑问。我肯定,连它也由两人组成:一个与人为善,通情达理;另一个则让我心里发毛。它只是偶尔显现,但始终突如其来,让人胆战心惊。它于是像自言自语,但所言针对我,通常直抵内心,往往令人哑口无言。
我想得起来的第一个事例发生在我六岁,还未上学时。那时邻居的家境尚可,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儿子,年纪跟我相仿,他还有两个妹妹。他们其实是城里人,尤其在周日捯饬孩子,我觉得可笑——锃亮小鞋、花边短裤、小白手套,即使工作日里,孩子们也梳洗得干干净净。娃娃们胆怯地远离我这个大淘气包,举止文雅,我裤子破口开绽,鞋子百孔千疮,双手肮脏。家母没边没沿地比较、告诫,让人怒气冲天:“看看这些可爱的孩子,他们温文尔雅,可你是个无法对付的野小子。”此类告诫令人激动,我决定揍扁那男孩,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母亲对遭此横祸怒火中烧,赶忙到家母那里言辞激烈地抗议我的暴行。家母因此震惊,声泪俱下,我还从未经历过她如此长篇累牍地训话,自己没有意识到过失,而是满足地回顾所作所为,因为似乎有点抵消了我这个外人在本村的格格不入。家母大为光火,我深受触动,懊悔不已,缩到家里那架老旧拨弦古钢琴后面我的小桌旁,开始玩积木。良久,一片寂静。家母退回窗边位置织毛线。我听见她喃喃自语,从耳朵里刮到的只言片语可以推断,她放不下那件事,但这次意思相反,听上去好像有点为我申辩。突然,她大声说道:“当然也根本不该养着这么一群小崽子!”我也忽然知道,她说的是捯饬过的“猴崽”。她至亲的兄弟是养狗的猎人,总是说育狗、杂交、品种与下崽。我松了一口气,断定连她也认为这些可憎的孩子是劣等杂种,所以,她的训话当不得真。但我当时就知道,得默不作声,绝不能洋洋得意地责备她:“瞧,你的看法也跟我的一样。”——因为她会愤怒地回敬道:“臭小子,怎么能给你妈编派这样的粗话!”我由此推断,想必先前已经有过一串类似经验,我却忘了。
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开始怀疑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件事,表明家母的二重性。有一次吃饭时说到,某些圣歌多么无聊,说到是否可能修改圣歌集时,家母嘟囔道:“啊,你是我的爱,你这该死的至福。”我又跟先前一样,装得好像什么都没听见,虽有胜利感,还是小心避免张扬。
家母身上两种人格相去甚远,所以我孩提时常做关于她的噩梦。白天,她是可爱的母亲;夜间,她让我觉得毛骨悚然。于是,她如同先知,又是怪兽,仿佛熊穴中的牧师,古远而寡廉鲜耻,像真相与天性一样无羞恶之心。她就是我所称“天心(natural mind)”[3]的化身。
我在自己身上也看出一些这种古远天性,它赋予我并非总是惬意的天赋,识别人和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不想承认某事,就蒙蔽自己,虽然可能受骗,但其实确知情况如何。“符合实际的认识”基于本能,或者依据与他人神秘互渗。可以说,是“背后之眼”在公事公办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