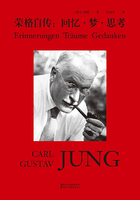
第7章 中小学时光(4)
后来遇到奇事时,我才更好地领会这点,如我曾讲述一个不相识者的生活经历。那是在我妻子一名女友的婚礼上,我根本不认识新娘及其家人。吃饭时,坐在对面的是中年美髯公,有人介绍他是律师。我们起劲地谈论犯罪心理学,为了回答他某个问题,我想出了一个案子,添枝加叶。我还在说着,发觉对方神色大变,座中静得出奇,我狼狈地打住话头。谢天谢地,我们已经在吃餐后点心,我不久就起身走入旅馆大堂,溜到一角,点燃一支烟,试图考虑是什么情况。此刻,来了同坐一桌的一名先生,对我指责道:“您怎么会如此冒失?”——“冒失?”——“对,您讲的这个故事!”——“这可是我虚构的!”
情况表明,我讲述了对面那个人的故事,包括所有细枝末节,这让我大吃一惊。此刻,我还发现自己想不起从头到尾讲述过程中的任何一句话,至今依旧难觅整个故事的踪迹。海因里希·乔克[4]在其《自省》中描写了一次类似经历,他在一家小饭馆揭穿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是小偷,因为他的内心之眼发现后者有偷窃行为。
我平生常常忽然知悉的确根本不可能得知之事,觉得好似自己想起知情之事。家母亦有类似情况,她不知自己说过什么,而像是一个绝对权威的声音正好说出适宜之言。
家母多半认为我远比实际年龄老成,像对成年人一样跟我说话。看来,她把不可能告诉家父的一切都跟我说了,使我过早成为熟悉她百忧千虑的知己。大约十一岁时,她告诉我涉及家父的一件事,令我惕虑。该怎么办,我绞尽脑汁,得出的结论是,得向家父的某个朋友讨教,听说他是手眼通天的人物。我未对家母透露片言只语,就在一个无课的下午进城,按响了这位先生家的门铃,开门的女仆说主人外出了,我失望、郁闷地又回家了。但我倒可以说,他不在家是特别神佑(Providentia specialis)。随后不久,家母在谈话时又重提此事,这次她的讲述截然不同、无关紧要得多,一切都是障眼迷雾。这让我深受打击,心想:你是驴,相信此事,呆头呆脑地当真了,差点闯祸!——从那时起,我决定,把家母所告知之事打对折。对她的信任有保留,而这每次阻止我把萦怀之事告诉她。
但有的瞬间,她的第二人格爆发,而她那时所言总是“说到点上”,而且符合实际,我为之颤栗。若此时抓住家母的话不放,我就会有对话者了。
家父的情况却不同,我本该把自己的宗教麻烦对他摆明并向他求教,但没这么做,因为我似乎知道,出于值得尊敬的原因,由于他的职务,他会不得不回答什么。不久之后就证实了这一猜测多么在理,家父在教无聊透顶的坚信礼课程。一次,我在翻阅《教理问答书》,要找出听上去不多愁善感、还不会难懂、无趣的关于“我主耶稣”的阐述。我就碰上了关于上帝三位一体的段落,这就是激发兴趣之事:一种统一同时是三位一体。这是一个问题,它的内在矛盾吸引了我。对我们要讲到此问题的那一刻,我迫不及待。时候到了,家父说道:“我们现在该讲三位一体了,但要跳过,因为其实我不明就里。”一方面,我钦佩家父的诚实;另一方面,却深感失望,心想:果不其然,他们一无所知,也无所思虑。那我能说什么?
我在显得善于思考的某些同学那里试图旁敲侧击,但徒劳无益,没有共鸣,倒有诧异,这令人警醒。
虽然无聊,我还是竭尽全力强迫自己不加领会就信仰(似乎与家父的态度相应),准备参加寄托着自己最后一线希望的圣餐礼。虽只是纪念餐,对1890-30=1860年前谢世的“我主耶稣”的纪念活动,但他可是做了某些暗示,如“领受吧,食用吧,这是我的躯体”,意指圣饼,我们食之当如食本为肉身的圣体,我们同样当饮本为圣血的酒。我领会了,我们应以此方式把他摄入体内。不过,这让我觉得显然不可能只有一项重大秘密隐藏其后。在家父似乎极为看重的首次圣餐仪式上,我会亲身体验,对圣餐的准备主要在此期待上。
按惯例,我的教父是一名教堂执事,沉默寡言的老人让我心怀好感,常在作坊看这名造车匠人在车床旁用木匠斧灵巧劳作。他身着礼服大衣,头戴大礼帽,郑重其事地来领我去教堂。家父身穿熟悉的法衣,立于祭坛之后,朗读着祈祷书中的祷词。祭台上有放着小面包块的大盘。依我看来,面包出自那个面包师之手,他提供的面包乏善可陈、寡淡无味。从一把锡壶里把酒注入锡杯,家父吃一小块面包,饮一口酒,把杯子传给一名老翁,我知道事先从哪家酒馆打的酒,觉得大家都拘谨呆板、郑重其事、无动于衷。我紧张地注视着,却看不出、猜不到,他们身上是否发生了什么特别之事,就像所有教会仪式、洗礼、葬礼等等一样。我的印象是,此处做了什么,以合乎传统的方式实施了什么。连家父也似乎努力首先中规中矩地行事;还要抑扬顿挫地说话得体或诵读合宜。无人提及耶稣死后已有1860年,在其他纪念活动上可是突出这点的。我看到无悲无喜,鉴于受纪念人物的非凡意义,感觉这一纪念活动在任何方面都羸俭异常,与世俗周年大庆绝对不可比肩。
突然就轮到我了,面包吃起来淡而无味,不出所料,只抿了一小口的酒又淡又酸,显然不是上好的。然后是终祷,大家向外走去,既不闷闷不乐,也不心怀喜悦,而是面部表情告诉人:“好了,就这样了。”
我随家父回家,强烈意识到自己头戴黑色新毡帽,身穿黑色新西服,它都快成礼服大衣了,那是加长的夹克,下摆向内放宽成两片,中间是开衩,口袋里可以放手绢,我觉得表示男子成年。我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隐约加入男子汉的行列;今天午餐还有特别的珍馐佳肴。我会整日穿着新装四处溜达,否则会没着没落,根本不知是何感觉。
不过,在随后几天中,我逐渐明白,什么也没发生,虽曾到达有所期待(不知是何)的宗教入门顶点,但什么都没出现。我知道,上帝可能让我遭遇闻所未闻之事、火与超凡之光,但至少对我而言,这场纪念活动丝毫不见上帝的踪影。虽然说到他,但只是言辞。即使在其他人身上,我也未曾感知不知所措的绝望、深受感动和喷涌的圣宠,这些对我而言是上帝的实质。“领圣礼(communio)”、集于一身或者合一无迹可察。与谁合一?与耶稣?他可是死于1860年前的一个人。为何要与他合一?他号称“圣子”,似乎就像希腊英雄那样是半神,那凡人如何能与他合一?人称此为“基督教”,但依我对上帝的体验,这一切的确与他无关。而一清二楚的是,是耶稣那人与上帝有关;宣扬了上帝作为好父亲爱人、善良之后,他在客西马尼园和十字架上绝望了,但他于是也看到了上帝的可怕,我可以理解。但为何还要有用如此面包、此等酒的这场寒酸的纪念活动呢?我慢慢明白,圣餐是灾难性的经历,以一无所获收场,更有甚者,是惘然若失。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参加这种仪式了。对我而言,它并非宗教,是上帝缺位。教堂是不可再接触之地,于我而言,那里没有生命,而有死神。
对家父的强烈同情裹挟了我,我对他的职业、他的人生的悲剧性恍然大悟,他确与拒不承认的死神搏斗。他和我之间裂开一道深渊,而我看不到跨越这条无尽鸿沟的可能性。父亲可亲可爱,豁达大度,在许多事上听我自便,从未专横以待,我不能把他推入那种绝望、那种亵渎神明的境地,即便它们为经历圣宠所需。只有一个神能这么做,我不得造次,这太不人道。我想,上帝不近人情。不让人性靠近他,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他善良而可怕,兼而有之,因此是巨大的危险,面对它,人当然试图自救。人一厢情愿地依附于他的爱与善良,以不至于落入诱惑者与毁灭者之手。耶稣也注意到这点,所以训诫道:“别诱惑我们。”
我与教会、与所了解的人类环境一致,这让自己伤透脑筋,觉得遭受了生平最大挫折。我觉得宗教观是与这一切唯一意味深长的关联,它土崩瓦解,亦即我再也不能苟同普遍的信仰,反倒发现自己陷入不可言宣之事,陷入不可与人共有的“我的秘密”。这很吓人而且(最糟糕的是)粗俗可笑,是魔鬼的笑声。
我开始冥思苦想:该对上帝有何看法?我并未自己突然想到上帝、大教堂,更别提三岁时侵袭我的那个梦,是比我的意志更强烈的意志把两者强加于我。是自然在我身上做了此事?可自然无非就是造物主的意志。为此谴责魔鬼也无济于事,因为它也是上帝的创造物。仅有上帝是实际存在的,是破坏之火,是无法描述的恩宠。
圣餐失灵了?是我失败了?我严肃认真地做了准备,希望经历圣宠与启悟,但什么都没发生,上帝依旧缺位。为了上帝的缘故,只要教会、家父和其他所有人的信仰代表这个基督教,我就觉得自己与它们格格不入。我自外于教会,悲哀萦怀,笼罩了开始大学学业之前的所有岁月。
三
有什么书能够告诉我,关于上帝,人都知道些什么,我开始在家父的藏书中寻找那些书,藏书虽少,当时却显得可观。起先只找到传统观点,但并非我所寻求之事,也就是独立沉思的作者,直到遇见比德尔曼1869年所作《基督教教义学》。看来有人自己深思熟虑,自有主见。我获悉,宗教是“人自我关涉上帝的思想行为”。这使我很抵触,因为自己把宗教领会成上帝对我所做的事;宗教是上帝的行为,我简直是听其摆布,因为他是强者。我的“宗教”与上帝就没有通情达理的关系,因为我对上帝知之甚少,怎么可能以这样的事为依据?所以,要与上帝有缘,我就必须更多了解上帝。
在《上帝的本质》一章中,我发现,上帝表示自己是“神人同格”,“可以比照人的自我作想象,而且是独一无二、简直超凡脱俗的自我,全世界就是它”。
据我对《圣经》的了解,这一界定似乎确实。上帝神人同格,是宇宙的自我,正如我是本人心灵与躯体外表形态的自我。此处,我却遇上了巨大的障碍:神人同格的确可能是一种特征。特征不是其他事,就是说,属性是特定的。但若上帝是一切,他如何还能拥有可区别的特征呢?但若他具有一种特征,则他只能是主观受限世界的自我。而他有怎样的特征或者怎样的位格呢?一切确乎系于此,因为否则无法以他为依据。
我竭力抗拒比照本人的自我去想象上帝,这让我觉得即使不是渎神,也是狂妄无比,反正觉得“自我”是难以把握的事实。首先,对我而言,这个因素有两个自相矛盾的方面:头号自我与二号自我;再者,这种形式与别种形式的自我是极其狭隘之事;它受制于一切可能的自欺、迷误、情绪、情感、热情与罪孽,负多胜少。它幼稚、虚荣、自私、执拗、需要呵护、贪婪、不公、敏感、慵懒怠惰、不负责任,诸如此类。遗憾的是,它缺乏我艳羡赞赏的别人身上的许多美德与天赋。难道我们就要按照这种类比去想象上帝本质?
我孜孜不怠地寻找上帝的其他特性,发现它们也都是我从坚信礼课中已经了解的。我发现,根据第172条“上帝超凡脱俗最直接的表现首先是负面的,‘人看不见他’,诸如此类;其次是正面的,‘他居于天国’,诸如此类”。这是灾难性的,因为我马上想起渎神的图景,上帝直接或间接(通过魔鬼)把它强加于我。
第183条教导我,“与合乎道德的世界相比,上帝超凡脱俗的本质”在于其“公正”,其公正不仅是“判决”公正,而且“标志其神圣本质”。我希望在这一条中对上帝的暗事阴私有所闻知,它们让我折腾,要闻知他的报复心、危险的气性、对处于自己无限威力之下受造物做出令人费解的举止。凭借其万能,他必定知道它们多么不顶用。但他还要引诱它们,或者考验它们,虽然一开始就知道实验的结局。——是啊,上帝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此行事的人物是什么呢?我不敢想象,接着竟然读到,上帝“虽则独来独往,除了自己,本身无需什么”,“由于自己要称心满意”而创世,“使自然界充满他的善意”并“意欲用他的爱充盈合乎道德的世界”。
起先,我反复琢磨“称心满意”这个令人讶异的词,对什么或者对谁称心满意呢?显然是对世界,因为他称誉自己的日常工作,但我从未领会的恰恰是这点。当然,世界美好无比,但也同样令人生畏。乡间小村,人稀事少,对“老、病、死”的体验比别处更深入、详细、不加遮掩。虽还不满十六岁,我对人和动物生命的实情司空见惯,在教堂与课堂上听够了世界的疾苦与堕落。上帝至多能在天堂感受到称心满意,但即使在那里,他自己确实也设法让这种美妙不能持续过久;在伊甸园置入危险的毒蛇——魔鬼真身。他对此也称心满意吗?我深信不疑的是,比德尔曼不这么认为,由于宗教课越来越显眼地那般无的放矢、漫不经心,他干脆信口开河,劝人虔敬,根本不曾察觉自己在胡说什么。我本人虽然不假定上帝残忍地对人与动物无辜受苦受难感到心满意足;但觉得绝非荒谬的是设想他有意创造一个充满对立的世界,其中一物吞噬另一物,向死而生。自然规律“奇妙的和谐”更让我觉得是勉力抑制的混乱,而“永恒的”星空与定轨明显是无序无谓的偶然事件叠加,因为所谓星座其实根本看不见,只是些任意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