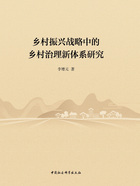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权下沉的乡村治理体系
一 国家稳定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乡村治理层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政权体系,实现国家稳定是当务之急。首要便是构建新的乡村政权体系。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等。根据这些法规、法令,我国乡村基层政权体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区、村体制,即在县以下设立区政权和村政权,通过人民代表会议产生区村两级政府,进行地区行政事务处理。在村级场域中建立政权组织成为党巩固革命成果的重要方式。[30]另一种是区乡建制,在县之下设立县政权的派出机构即区公所,在区之下设立乡政权,通过乡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乡政府。[31]1951年《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应酌量调整区、乡(行政村)行政区划,缩小区、乡行政范围,以便利人民管理政权”[32]。根据国家政策指示,地方政府进行乡级行政区划的重新规划,缩小乡的规模是其重要内容,并通过设立区,发挥区的中枢作用来强化县对乡镇的管理。乡与行政村并存,同为农村基层行政区划,乡的规模由一村或数村构成,户数在100—500户之间,人口在500—3000人不等,这种乡建制被称为“小乡制”。行政区划规模的缩小,使得乡政权的数量不断增多,北京、绥远、上海等省市增长了2倍多,河南、广西、云南等新解放地区增长了5倍多。通过调整,乡级政权的辖区范围大大缩小。
土地改革完成后,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开始。1954年中共中央指出,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和合作化运动发展,要求乡的规模要适宜扩大,不宜设立太小,乡设立太小的省市需要进行必要扩大。1955年,全国开始推进“并乡撤区建社”,增大乡的规模。以禹县为例,1955年12月为促进高级社建设,禹县对全县乡政权进行调整,调整之前其乡政权为193个,每乡平均632户,3163口人。与此同时,1956年2月,与高级社的成立同步,调整后保留26个中心乡和75个一般乡。并乡的范围、原则和条件如下所示:(1)并乡的范围:根据上级指示和地方实际,全县193个乡政权,其中45个山地乡原则上不变,148个平地小乡合并成65个大乡。在人口规模上,以2000户、8000口人左右为适宜规模。(2)合并的原则:以原有的规划界限为基础,注重自然条件和方便原则,根据乡的工作运作尽可能保留重点乡,注重重点乡、中心乡、一般乡的互补与联系。(3)并乡的条件:交通方便,人口集中,工作基础好。[33]在高级社规模上,一般以乡的行政区域进行建设。例如,郭西和郭东所在的高级社是由原来的郭连乡转来的,该高级社所处的禹县全县共建成高级社17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7%。每社平均761户;在1955年到1959年,禹县基层建制进行四次调整。[34]在这一过程中,乡、社规模不断变化,它们对适应和促进生产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频繁的变动中,村级政权建制逐步弱化,职能也逐渐被合作社替代。
二 政党下乡塑造的乡村领导组织体系
正如亨廷顿指出的,“一个政党要巩固政权基础,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向广大乡村地区延伸,将传统农村组织起来”[35]。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代表,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最终摆脱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与压迫,实现了人民大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巩固新生政权,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由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全国政权组织体系,将权力下沉基层社会。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防止投机分子等加入党组织,在新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极为慎重地成立党组织和发展党成员。“随着土改的完成和合作化运动陆续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的方法发生转变,从通过党的工作队的领导,转变为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来领导”[36],强调要在乡、村普遍建立党支部,推动政党下乡。通过“政党下乡”,马铃薯状分布的农民整合起来,成为党的组织网络中的一员;并且具有了政治意识,使乡村社会得到真正的改造。[37]1954年《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从国家层面规定农村发展党组织的步骤与方式,指示在乡村发展党的组织,要求在没有党的组织的12万个新区乡村、2万个老区乡村成立党的组织。[38]到1954年11月,全国22万个乡中,有17万个乡已成立党的组织。[39]总体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村党组织发展较为迅速。
在乡级党组织建设及发展新党员过程中,上级县委或区党委进行有效控制与引导。以上海郊区为例,土改完成后,上海区党委积极开展有序的党组织建设,通过四十天培训,建设了11个乡党组织,发展42名新党员。农业合作化更是加快了党组织在农村的建设和发展。1954年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组织工作会议对农村党组织建设做出一系列新规定,加强乡党组织统一领导,在党员人数超过50的乡,可以建立党总支,在农业、手工业合作社中设立党小组,人数多的可以建立党支部。这一规定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建设上的重大转变,不仅将党组织普遍下沉到乡这一级,更是将党组织延伸建立于行政村和合作社中,而且加快了党员发展速度,使党组织成为乡村全面建设的真正领导力量。合作化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党组织下沉,形成了自上而下延伸和覆盖农村社会的组织网络。党的支部由行政乡一直延伸到村庄和生产单位,“支部建在村庄”和“支部建在生产单位”成为其下沉表现。[40]通过政党下乡,乡级党组织、村党组织体系逐步完善,夯实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层组织基础,从组织上制度上密切了党与农民的联系,党的领导体制也进一步延伸到乡村社会末端。另一方面,党组织深入村庄极大改变了村庄权力结构,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权力核心,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领导核心,成为乡村治理的领导者。
三 行政下乡塑造的乡村行政管理体系
现代社会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开始加强乡、行政村政权建设,逐步构建新型行政管理体系,加强对乡村的管理,并通过行政下乡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家就着手废除原有的保甲制,新的解放区积极开展清匪反霸、土改等运动,废除乡里制度,成立新的乡、村政权。如湖北省1948年建立了1276个乡政权,废除保甲制度,通过改组和合并等方式改组保甲以建立村庄,到1950年湖北省通过改组形成18037个行政村。1950年《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在全国建立行政村与乡一级地方政权机关,对其产生方式、职权、人员做出明确规定。1954年《关于健全乡政权组织的指示》指出,乡人民政府按生产合作、文教卫生、治安保卫、人民武装等工作设置工作委员会。例如据西北局调查,除政府以外,还有负责生产、文教、治安、调解等工作20种委员会。人员更多根据职务进行设置,例如,1952年衡山县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划小区、小乡及乡级编制供给的决定》,全县共设17个区,270个乡、4个区属镇、1个县属镇。在政府内设乡(镇)长 l 人,副乡(镇)长1—2人,另有生产、财粮、治安、调解委员各l人以及一名秘书。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的职能为“具体执行上级政府的决议和命令;具体实施村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并经县、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决议案;掌握与管理村财政的收支;统一领导和检查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作,乡村人民代表会议做工作报告”[4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行政村与乡政府一样是国家一级政权机构,是国家政权组成部分。
在乡村治理层级上,《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最低一级的乡或行政村隶属于区人民政府。同时,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乡行政村人民大会,作为民主议事和决策机构。人员安排上,行政村通过代表会议制选举产生村长和若干委员。在职能规定上,《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第四条对行政村职权做出规定,行政执行职能是行政村首要职能。乡、村作为一级行政组织,村政权接受乡政权行政领导,村长、副村长由乡政府任命。行政村设村主任1人,副主任1—2人,村的正副主任在乡人民代表中推选或由乡人民政府委员兼任。[42]通过行政下乡,村庄成为行政体系的基础,有效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的行政领导。这无疑是现代国家行政建设的重要一步,它对国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动员与整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行政村的性质进行重新规定,行政村从国家政权机关转变成为乡一级行政机关的派出组织,协助乡人民政府开展乡村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任务呈迅速扩张趋势,行政机制全面介入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全能型治理结构。[43]只不过,基于时代发展要求及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强化行政下乡全面介入乡村社会进程中,行政管理体系也在不断调整,但都是以构建强大的乡村行政管理能力为重要目标。
四 重构的群众性组织及乡村经济社会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党下乡、行政下乡过程中,乡村社会组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个重要变化是传统宗族组织瓦解。在传统乡村社会,宗族组织具有正式权力特性,一直在乡村占据重要地位,在乡村治理中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在新政权下沉中,禁止宗族活动,没收族田、祠堂等各类宗族财产,国家更通过土改运动和合作化运动瓦解了家族存在的经济依靠,使其彻底失去存在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通过阶级化实现家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在阶级化中划成分是其中重要方式。[44]例如,四川双村在解放之际,82岁刘氏族长因为不是地主,没有过多的财产,而且在村庄建设、社会秩序维护上发挥着较好的作用,在政治上没有被冲击。在土改运行中,刘洪发在划成分中被划为贫农,也不再具有宗族领袖的身份,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工作的开展,宗族也彻底失去了存在的价值。[45]总体来看,随着新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旧社会组织逐步消失,传统宗族权威式微,为新社会组织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与之相适应,在党的有力领导下,广大农民重新被组织起来,与新政权相适应的诸多新型组织得以蓬勃发展。其中,共青团、妇联、民兵连、贫下中农协会等群众性组织是其中的代表。1951年统计,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个行政区农民协会会员约有8800余万人。同时,民兵组织在全国村庄普遍建立,民兵规模已达到1280余万人。[46]以安徽省为例,到1952年,加入各类组织的群众已有1459.34万多人,其中农协772.57万人、妇联会员413.43万人。农村群众性组织活动主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自上而下的党组织决策是群众性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和依据。例如共青团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将广大农村青年组织起来,围绕在村党组织周围,协助党支部完成各项工作。通过群众性组织建设,逐步形成了从县级群众组织到乡级群众组织到村级群众组织的组织体系,使政权延伸到乡村基层社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对乡村社会有效净化与政治整合,逐步夯实了新政权的基层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新型经济社会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两次大规模乡村改造运动,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和合作社两个新经济组织,通过经济要素把分散的农民个体联系起来。对于农民协会,1950年《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对农会性质做出说明,农民协会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是“农村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这使得农会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权力机关特点。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是农民代表大会制政府,农会可以代替乡(行政村)政府行使基层行政权,承担着临时性政权职能。农民协会干部由农民协会委员会互推的主席、副主席构成,农村的贫下中农都可自愿入会,在获得农协委员会批准后就成为协会会员。例如,湖南省衡县各乡(行政村)在区人民政府主持下,由农协会员或农协代表在农协会会员大会或农协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正副乡长和乡农民协会主席和副主席。对于自然村,由乡(或行政村)政府指派行政组农民协会组长、副组长等人员,其中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和具有良好德行的知识分子是主要指派人选,由其负责组内事务。[47]总体来看,农民协会在团结群众、培养干部、改变乡村政治格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满足工业化发展需求,国家大力推动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高级社农户占全部农户的87.7%。[48]在组织结构上,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初级社阶段的权力机构是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其领导层由社长、副社长、会计、农业委员、保管等组成,初级社下设小组,合作社很多时候行使行政村的功能。以四川双村为例,刘兴才仍然是村长,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工作都在初级社进行,行政村已成为乡政权向合作社下发指令的中转辅助机构。[49]高级社内部设有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设立社主任和副主任等。社员大会是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管理委员会是由管理委员会主任领导的执行机构,下设分管农业、副业、财务、保卫等工作的委员若干人。监察委员会是监督和督促机构,监察委员会设主任和若干委员。高级社设置了许多直接联系农民的生产性组织,称为作业组,设有组长和计工员。例如,岳村的行政6组分为岳上屋耕作组和下屋耕作组。上屋耕作组有46户,213人,下屋耕作组有39户,196人。这些耕作组(有的地方也称为作业组),设有组长和计工员。[50]从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可以看出,社员大会是合作社最高权力机构,由组员或社员推选互助组组长或合作社社长,由其领导召开社员大会,在听取社员意见的基础上进行日常管理和重大决策。高级社在安排生产的同时也承担行政管理职能,代行村级政权职能,实行村社合一制。从农村社会权力构成上来看,纵向上国家政权下沉到了社、队层面,横向上扩展到了农民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随着高级社的普遍建立,全国农村“村社合一”的政权形态逐步形成,高级社构成了我国乡村基层政权的新基础,推动形成了新型的乡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