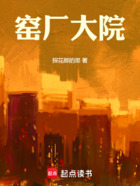
第16章 唐栀
郭灶火蹲起身,心说哪个窝俊姑娘来找我?
老四郭香和大爷家的三姐郭倩都漂亮,别的漂亮姑娘我不认识啊!
每个地方对父母,叔伯,爷爷辈的称呼不同。
这边管父亲的父亲叫老爹,管老爹的兄弟和同辈的人叫大爹,二爹,三爹,小爹,称其配偶为大奶,二奶,小奶;
管父亲的亲兄弟或五服(五辈)内的兄弟叫爷,比如大爷,二爷,三爷,小爷,称其配偶为大娘,二娘,小娘。
出了五服的都叫叔,婶,这样能分出叔辈关系的远近。
有一些庄子里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个姓,都叫叔分不出血缘关系的远近,有了爷和叔,远近顿分。
在郭灶火父亲郭有铜这一辈,还是延续几十年前的尊称,管父亲叫答,母亲叫娘。
女婿管丈人叫“大”,管丈母娘也叫“娘”。
到了郭灶火这一代,才称父母亲为爸妈,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延续之前的称呼。
全国各地的叫法不一样,有的地方管父亲的哥哥叫大伯,二伯,三伯;管父亲的弟弟叫叔,比如二叔,三叔,小叔。
而“叔”这个称呼太大众化,走大街年纪大都可以叫叔。
叫叔,总给人不亲的感觉,像是叫外人。
还有地方叫称父亲的兄弟为“答”,比如二答,三答,小答。
而郭灶火他们这里的“二答,三答,小答”是骂人的话,而且是极其恶毒的,意思是母亲的情夫,姘头之类的。
总之各个地方的风俗人情不一样,对长辈和晚辈的称呼也不相同,但入了乡就得随俗,不然闹出笑话事小,因为语言称呼而搞出冲突,甚至弄出人命的事也发生过,那就不值得了……
……
可三姐在外地上大学,不可能来找自己。
老四在县城里上高中,这不前不后的应该不会回来,就有事回来也应该回家找父母。
郭灶火的大爷叫郭有金,育有三女一男,大姐郭红和二姐郭兰都已出嫁,三姐郭倩在外地上大学,二哥郭书豪在本公社中心小学教书。
会是谁来找我呢?
郭灶火穿上衣服,轻手轻脚关上门,出了房间。
春风吹来,艳阳高照。
郭灶火抬头看天空,天空很蓝,太阳当空晃的他眼花,大院子里有几户人家门口炊烟袅袅,水井边围着几个妇女在淘米洗菜,一副人间烟火图。
胡老三的房门落锁,应该是在窑厂办公室,或者在派出所。也不知道蒋庆丰那事怎么弄的。
现在先不管,也管不了,人他给抓到了,剩下的就交给公家了。
大院里的食堂大概在十二点半左右才开饭,因为早晨都是七点半开饭,中午十二点半开饭,晚上六点钟开饭,庄稼人都是这样吃饭。
出了大院,外面一下子就热闹起来,白天出砖的工人穿着薄裤短袖,脖子上搭着黑乎乎的毛巾,推着独轮车在窑室里进进出出,满头满脸都是红色灰尘和碎砖末子。
这个季节中午的气温较高,如果不干活只穿件薄棉袄即可,可干窑室这种重活连毛衣都穿不住,再加上白天窑室里的气温更高,所以出砖人感觉是在过夏天,时不时拿毛巾擦汗。
在那些已经出好的码砖区,一些拉砖的车夫正在往车上装砖,他们也穿着单衣,但不流汗,拿砖、码砖的动作单一而机械,每个人看上去都很疲惫,和他们同样疲惫的还有他们的骡马,看上去也都无精打采的站在大车边上吃草料,有气无力的甩着尾巴。
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早晨从窑厂把红砖装上车,然后赶马车拉到货主家再一块块卸下来码整齐,期间不但不能坐车上,遇见坡坡坎坎什么的还得头伸着帮牲口拉边挂,卸好后又马不停蹄的回到窑厂装车,装好了再返回,直到晚上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
出砖人苦,拉砖人也苦,拉车的骡马还有休息时间,他们没有,冬天风吹挨雪,夏天日晒淋雨,让他们看上去非常苍老,干瘦干瘦的活像黑褐色机器人。
“灶火,今天怎么起来这么早?”
柳爱芳说着左手叉着膝盖直起腰,右手拳头虚握捶腰,满脸的疲惫。
她头上顶着有些发白的蓝色方巾,穿一身蓝布做的打满补丁的粗衣裤,脚上穿着有点露大脚趾的黄胶鞋,刚才拿着铁锨在捡地上的碎砖头往独轮车里放。
这些地方的砖刚被拉砖人拉走,剩下一地的碎末子需要打扫。
柳爱芳在窑厂里干杂活,什么活都干,忙的时候还得充当机动人员,哪里缺人去哪里,一个月三十块钱死工资,从早到晚手脚不闲,没有休息天,下雨天别人休息,她得去厂里疏通水道。
为了养活两个孩子,无论是谁让她干活都是随叫随到,就像一头老黄牛。
“大姑,外面有人找我!”
“哦哦!那快去吧!”
柳爱芳说着,弯下腰捡砖头,一缕灰白的头发从方巾里垂下。
郭灶火走到大门口,一辆空驴车从门外驶了进来,带来一股灰尘,拉车大叫驴的脖子上系着一个铃铛,随着它疲惫的步伐一荡一荡的响,这相当于汽车的喇叭,告诉行人避让,有车子来了。
出了大门口,郭灶火四处找人。
“灶火!”
一个脆生生的声音,在大门北侧的一棵大槐树底下响起。
“栀子姐?”
郭灶火眼前一亮,小跑过去。
来人是唐栀,小名栀子,是郭灶火姐姐郭凤的同学,初中时在他家借宿住过三年,郭灶火一直叫她栀子姐。
唐栀和郭凤一般大,今年二十一,一身粗布蓝色衣裤也遮不住她高挑有致的身材,脚穿一双松紧口千层底,白袜子,唇红齿白的,大眼睛,一条乌黑大辫子垂在胸前。
“灶火,中饭吃了吗?”
见郭灶火孩子般朝自己跑来,唐栀心里一热,他在郭家借宿三年,郭家人对她都很好。
“还没呢。我说是哪个窝俊姑娘找我呢,原来是栀子姐。”
只一眼郭灶火就看出唐栀的眼睛里有血丝,曾经清澈见底的眼神被忧郁取代。
唐栀家距离这里有八九里地,上初中时要上晚自习,最后一节课下课已是八点半,她一个女孩子回家要走一个多小时,每天是她哥每天晚上赶驴车来接她,早晨再送她来学校,但遇见刮风下雨或农忙的时候就会晚点。
有一天晚自习下课,郭凤回到家才发现作业没带回来,便让灶火陪她回校拿书,在校门口看见唐栀一个人可怜巴巴蹲在风口里流眼泪,问了才知道她等哥哥来接。
于是郭凤和郭灶火一起陪着唐栀,直到她哥哥来把她接走。
回到家,郭凤把唐栀的事跟家人说了,老郭二话不说,让郭凤去跟唐栀说来家住。
那时候家里三间茅草屋,男孩们住一间屋,女孩们住一间屋,唐栀来了就在女孩们的屋里加张小床,一住就是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