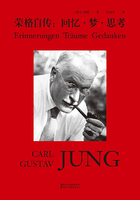
第12章 大学岁月(2)
当时,他越来越易怒、不满,这种状态让我满怀忧虑。家母避免一切可能让他发火之事,不做任何争执。虽则我不得不承认她的举止很睿智,却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然而,面对他情感爆发,我忍气吞声。但他显得容易接近时,我就经常试着跟他交谈,意在详细获知他内心的波澜起伏和自我认识。因为我有把握,有什么在折磨着他,我猜测,这与他的宗教世界观有关,他屡屡闪烁其词,我确信,那是对信仰的怀疑。我觉得,他缺乏必要经验,才会是这种情况。其实,我有意讨论时,就认识到必定有此类情况,因为对我提出的问题,或者他做的神学解答了无新意、枯燥乏味,或者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激得我反驳。我无法理解,为何他不抓住每个机会劲头十足地分析自己的处境。我虽然看出自己提出关键的问题让他悲哀,但我仍希望谈话有所裨益。我觉得几乎难以想象的是,他竟然会没有对上帝的体验——一切体验中最明显的体验。至少,据我所知,认识论认为人不可能证明此类体验,但我同样清楚,此类体验也根本无需证明,正如没什么必要证明日出之美或者证明有人害怕夜的世界。我试图以八成极其笨拙的方式让他了解这些不言而喻之事,满心希望帮助他承受不可避免落到他身上的异常命运。他的确非得抱怨谁,而他埋怨的是家人和自己。为何他不抱怨上帝这个让人捉摸不透的造物主,唯一对世界的苦难负有责任者呢?作为回应,上帝会给他送来那类富有魔力、深不可测的梦,上帝甚至不经询问就给我送来那些梦,就此注定了我的命运,我不知是何道理,但情况就是如此。上帝甚至让我瞥见他自己的本性,这种本性却是重大秘密,我对家父也不可或不能泄露。我觉得,如果家父能够领会对上帝的直接体验,我或许会向他透露。但与他交谈时,我从未走到那一步,连问题都没看见,因为我处理问题的方式侧重理智,不察言观色,尽可能避免感情,为的是远离他的情绪。但这种接近每次都如同红布作用于公牛,导致激怒的反应,令人无法理解,我理解不了为何完全合情合理的论据会遇到抵触情绪。
这些无果的讨论惹恼了他和我,我们最终都带着特有的自卑感退缩了。神学疏离了家父和我,我感到这又是灾难性的失败,自己却并不觉得孤独。我朦胧预感家父落入命运之手,无法摆脱。他很寂寞,没有可以商议的朋友,至少在我们身边的人里面,我不相信有谁说得出澄清问题的话。我曾听他祈祷,他绝望地力争保住自己的信仰。我既震惊又气愤,因为看出他多么无望地落入教会及其神学思想家之手,他们阻挡了他直达上帝的一切可能性之后,毫无信义地抛弃了他。现在,我深切理解自己的经历,上帝自己在我的梦中揭露了神学和建于其上的教会。另一方面,上帝像允许如此众多的其他事物一样允许神学。人可能推动此类发展,我觉得做此假设很可笑。人又算什么?他们像小狗、像上帝的一切受造物一样生来愚蠢而盲目,配给的一线光明无法照亮他们在其中摸索的黑暗。我有把握,而且深信不疑,所知的神学家中,无人目睹过“照入黑暗的光明”,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传授“神学宗教”。我对“神学宗教”无计可施,因为它不符合我有关上帝的经历,它要求人信仰,而人求知无望,家父竭尽全力地尝试过,失败了。家父同样不怎么能针对精神病科医生可笑的唯物主义而为自己辩护。这的确也是不得不信的事情,正如神学一样!我比任何时候都肯定,两者既缺乏认识批判又缺乏经验。
家父显然留有这样的印象,即精神科医生在大脑中发现了什么,证明在应该有精神之处存在“物质”而没有什么“气状物”,与此一致的是家父的一些告诫,我若学医,就不该成为唯物主义者。对我来说,他的告诫却意味着,我什么都不该相信,因为我知道,唯物主义者正如神学家一样相信自己所作的界定,而且我也知道,可怜的家父简直每况愈下。我认识到,始终得到颂扬的信仰不仅跟他,而且跟我认识的多数严肃的文化人搞了这个后患无穷的恶作剧。我觉得信仰的大罪是此事实,即它抢在经验前面。神学家从何得知,上帝故意安排了某些事物并且“允许”某些事物,而精神科医生从何得知,物质具有人的精神特性?我绝无耽于唯物主义之虞,家父却有此危险,我越来越明白这点。显然,有人跟他嘀咕了什么“暗示”,因为当时我发现,他在阅读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翻译的伊波利特·伯恩海姆关于暗示的书[6]。这对我新奇又重要,因为迄今为止,我只见过家父阅读小说或者比如游记之类,一切“聪明”、有趣的书似乎都是禁忌的。阅读却并未让他幸福。他的抑郁情绪日积月累,疑似病症也一样。几年来,他已经诉说有一切想得到的腹部症状,而医生无法下定论。现在,他诉说感觉“腹中有石”。我们长期没有当真,但最终,医生担忧了。那是1895年夏末。
春天,我在巴塞尔大学开始学业。平生唯一觉得无聊的时光,也就是中小学时期结束了,通往全科大学和学术自由的金色大门敞开了,我将会听到关于自然主要的真理,将会设法探悉关于人的一切,无论在解剖学上还是在生理学上,而与之相串联的将会是了解生物学特殊状态,亦即疾病。除此种种之外,我还可以参加佩戴标志的大学生联谊会措芬吉亚,家父就曾是会员。我是候补会员时,他甚至跟我一同参加联谊会远足,去了马克格拉菲兰德地区的一座酿酒村,在那里做了风趣诙谐的讲话,从中显现出他学生经历中的乐观精神,让我心花怒放。同时,我电光石火般地断定,他自己的生活随着学业结束而成定局,停滞不前,我想起一首大学生歌曲的一节:
他们低眉顺目,
复为市井之徒。
哎呀,哎呀,哎呀,
唉,事物变化多大!
这些歌词重击我的心灵。他的确曾经如我一样,是热情的大学新生;在他面前就如在我面前一样展现出世界,一样有无穷的知识宝藏。什么能让他颓唐沮丧、愤世嫉俗、萎靡不振呢?我不得其解或者答案太多了。他在那个夏夜把酒讲话,最后一次体味回忆他曾身处其中的时代,他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此后不久,他的状况就恶化了。1895年晚秋,他卧病在床,1896年初去世。
读完预科,我回家询问他的情况。家母说:“唉,老样子,他很虚弱。”他对她耳语些什么,她用眼神对我暗示他意识模糊,说道:“他想知道你是否已经通过了国家考试。”我发现不得不撒谎了:“是,很顺利。”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稍晚,我再次去看他。他一个人在,家母在隔壁房间干着什么。他喘着粗气,我看出他处于临终痛苦之中。我着魔似的立于床边,还从未看着人死去。突然,他停止了呼吸,我等啊等,等着下一次呼吸,这一口气没上来。此时,我想起了家母,走入邻室,她坐在窗边忙着毛线活。我说:“他死了。”她跟我走向床铺,看到他死了,好似惊讶地说:“一切都过去了,还真快啊。”
随后几天昏昏沉沉、令人痛苦,没留下多少记忆。一次,家母用她那“第二”声部对我或者对周围的空气说:“对你来说,他现在死了。”这似乎暗示我:你们不懂自己,他本来可能妨碍你。——我觉得这种看法与家母的二号人格一致。
这句“对你来说”让我深受打击,我觉得有一段旧日时光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另一方面,当时萌生了一丝阳刚之气和解脱感。家父死后,我搬进了他的房间,在家里取而代之,比如我得每周给家母家用钱,因为她不会勤俭持家,不会理财。
家父亡故约六周后,托梦给我。他忽然站在我面前,说休假回来了,因为休养得很好,就回家来了。我想,他会指责我,因为我搬进了他的房间。但他对此只字未提!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羞愧,因为以为他死了。——几天后,梦境再现,家父痊愈归家,我又自责,因为认为他故去了。我一再自问:“家父梦中复归,显得如此‘逼真’?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难忘的经历,首次迫使我深思死后是否有生命。
家父亡故后,我是否继续学业就出现了大问题。家母那边有部分亲戚认为,我该找个商行店员的活,尽快挣钱。小舅自告奋勇要帮家母,因为我们手头的钱远不足以度日。一个叔父帮了我,完成学业时,我欠他三千法郎。我当助教,私下出售不多的古董藏品,挣得了其他所需的款项,我从一个老姨母处接手了这些藏品,件件卖出好价,获利颇丰,甚是可心。
我不想忘却穷困时光,人要学会珍视平凡事物。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获赠一小箱香烟,就觉得很奢侈了,它们足够我抽一整年,只有周日时,才享用一支。
回首往事,可以说:大学时光是我的美妙时光。大家都有思想活力,那也是交友联谊的时光。在祖芬根人联合会,我以神学与心理学为题做了几次报告。我们兴致勃勃地交谈,绝对不止于医学问题:争论叔本华与康德,熟知西塞罗的各类文体,对神学与哲学感兴趣,可谓受过一切正统教育,要求有高雅的思想传统。
阿尔伯特·厄利是我最亲近的友人之一,我和他的友情维系到他去世(1950年)。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双方的父亲结交,我们的关系就开始了,比我们自己的年龄早大约二十年。但不同于因命运而渐行渐远的那些人,厄利和我不仅因命运而相会相聚,而且忠诚的纽带使我们戮力同心,至死不渝。
同为措芬吉亚联谊会会员,我结识了厄利,他十分幽默又感情丰富,是讲故事的好手。雅各布·布尔克哈特生活、活动在我们中间,我们巴塞尔的青年学生把他奉为已经具有传奇色彩的大人物,厄利是他的侄孙,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确实,厄利的某些神情、动作和说话方式显出这位稀世人物的一些外在气质。我偶尔在街上偶遇巴霍芬,就像遇到布尔克哈特一样,我也从这位朋友处获悉前者的某些事。但比这些鸡毛蒜皮更吸引我的是他深思默想,观察历史进程的方式方法,当时就已经成熟得惊人的政治判断力,对当代人物的理解深切中肯,令人诧异,他可以用笑话无与伦比地勾勒出他们的性格,无论他们怎么精心掩饰,他那怀疑一切的态度都能看出隐于其下的徒务虚名与空泛无聊。
我们盟友中的第三人是惜乎早逝的安德雷阿斯·菲舍尔,他后来长期担任小亚细亚的乌尔法市医院领导。在魏尔市的“老鹰”客栈和哈廷根城区的“希尔岑”客栈,我们在阳光下、在游移不定的月光下把酒讨论一切,这些谈话是我难以忘怀的学生时代的精彩时刻。
因为各自从业,天各一方,所以在随后几十年里见面不多。但厄利和我这两个同龄人年届中年这一隆重的时刻时,甚至命运都让我们更多重聚。年满三十五岁时,我们乘船同游,浑然不觉这值得纪念,就在我的帆船上,而苏黎世湖就是我们的海,当时在我手下工作的三名年轻医生就是船员。我们驶向瓦伦施塔特镇再返回,航程持续四天,迎着习习清风,扬帆航行。厄利随身带着福斯译的《奥德赛》,在航行时给我们朗读在喀耳刻处和下冥府的冒险奇遇。一抹光华笼罩在波光粼粼的湖上,两岸蒙着银光闪闪的薄雾。
“女神喀耳刻鬘云鬈发,仪态威严,声音优美,她让微风渐起,从后面吹向乌头船,鼓起船帆,陪伴我们顺风顺水。”
不过,在荷马描述的闪亮景象背后,我脑中不安地浮现出关于未来的想法,要渡过我们还要面临的大洋。此前踌躇不定的厄利,不久之后就结婚了,而命运就像对奥德赛一样赐予我下冥府,下到阴曹地府[7]。接着是战争岁月,我就又难得见他了,连高谈阔论也沉寂了,说的其实只是表层的事,但我们内心开始交谈,从他提出的某些零星问题可以猜到。他是冰雪聪明的朋友,对我相知甚笃,这种默契和他的忠诚不渝对我意味深长。在他生命最后十年中,我们又频频相见,因为两人都知道死神的阴影步步进逼。
在宗教问题上,我上大学期间受到许多启发。在家里有极可心的机会与一名神学家——先父的助理牧师谈话,他不仅胃口惊人,让我相形见绌,而且学识渊博,我跟他学到了教父学、教理史的许多知识,尤其获悉了关于新教的大量新知。当时常常提及里赦尔神学,它的历史观,尤其是以火车做比拟让我困惑[8]。就连跟我在祖芬根人联合会有过讨论的神学学生似乎都局限于基督生平所生发的历史效果这种理念,我觉得这种观点不仅弱智,而且过时了。突出基督,使他成为关于上帝和人的戏剧中唯一的关键人物,我不能苟同这种见解,觉得这与基督本人的看法截然相反,即基督死后,生育他的圣灵会在人群中取代他。
对我而言,圣灵意味着恰当地显示无法想象的上帝,他的作用不仅具有崇高的性质,而且如耶和华的事迹那样奇特甚至可疑,按坚信礼课程精神,我幼稚地把后者认同为基督教的上帝形象。(当时我也不知有了基督教才产生不折不扣的魔鬼这一事实。)对我而言,“我主耶稣”无疑是人,因而可疑,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圣灵的传声筒。这种离经叛道的观点与神学观相去甚远,当然令人极为不解。我对此感到失望,逐渐无可奈何,了无兴趣,此处唯有经验能够定局,我的这一信念越来越强。借用当时阅读的《老实人》的话,我可以说“这些说得都很好,但得耕作我们的园地”,意指自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