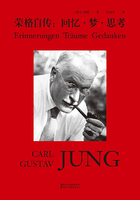
第11章 大学岁月(1)
虽然我对自然科学兴趣渐增,却仍时不时重拾我的哲学书籍。择业问题日益临近,令人焦虑不安。我极渴望结束中学时期,然后就会上大学,当然学自然科学,那样就会知道实际事务。我刚对自己近乎高调地许诺此事,怀疑就来了,难道不该是历史和哲学吗?再则,我又对埃及语和巴比伦语极感兴趣,最想当考古学家。但我没钱在巴塞尔以外的地方上大学,而巴塞尔没有这些领域的教师。我的计划很快就完蛋了,许久难做抉择,一再推迟做决定。家父对此很担忧,有一次,他说:“这小子对想得到的事都感兴趣,可不知想要什么。”我只能承认他说得对。高级中学毕业考试临近了,我们不得不做决定去哪个系,我毫不犹豫地说:上人文二系,就是自然科学,但让我的同学们怀疑的是,我指的到底是上人文一系还是二系。
这一貌似迅速的决定却有来历。几周前,就在头号与二号人格争做抉择时,我做了两个梦。头一个梦里,我走入沿着莱茵河延伸的昏暗森林,来到一个小坟丘——一座古坟旁边,开始挖掘,过了片刻,竟惊讶地发现了史前动物的骨头。这令人如痴如醉,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得了解自然、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还有我们周围的事物。
然后来了第二个梦,我在梦里又身处林中,林中水道纵横交错,在最暗处,我看到一个圆形池塘有茂密的灌木环绕。水中半浸半露地躺着最奇妙的物体,一个圆圆的动物五彩纷呈,由许多小细胞组成,或者由形似触角的器官组成,是一条直径约一米的巨型放射虫。这个壮观的物体不受干扰地躺在清澈深水中的隐蔽处,令人觉得不可思议,难以形容,激起我身上旺盛的求知欲,心怦怦直跳,就醒过来了。这两个梦强势地决定了我选择自然科学,消除了此方面的任何怀疑。
在此情况下,我明白了,生活在这个时代和特定地点,人理应得到自己生活,须为此目的而成为这个或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所有同学脑际萦回的都是这种必然性,根本不想别的事。我觉得自己奇怪,为何不能抉择定局呢?连那个学习费劲的D也肯定他会学神学,我的德语教师让我以他为勤奋认真的榜样。我明了,只能坐下来周密考虑此事了。比如,作为动物学家,我只能当教书先生,或者至多在动物园当个职员,就算要求不高,这也没有前景。比起教师生活,我却宁可选后者。
此路不通,我一闪念,可以学医,如梦方醒,奇怪的是,以前从未想到过。虽然我多有耳闻,祖父也曾为医,恰恰因此,我甚至对该职业有某些抵触。“千万别学样”是我的座右铭。现在,我心里却说学医至少从自然科学学科开始,就此而言,我就不会亏了。此外,医学领域多种多样,总还可能从事某一学术方向的活动;对我而言,“科学”是确定不移的,问题只是以何方式。我理应得到自己的生活,因为没钱,就不能为准备学术生涯而上外地大学,至多能成为科学的半吊子。此外,对我的许多同学,还有生杀予夺者(可解读成老师)来说,我生性还不讨人喜欢,引起猜疑和一片指责,也就无望找到能支持我实现愿望的靠山了。因而,我最终决定学医,伴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即以如此妥协开始人生并非好事。无论如何,做出这一不可收回的决定,我觉得轻松多了。
现在却出现难堪的问题:上学所需钱款从何而来?家父只能筹措一部分,但他向大学申请了助学金,我后来也拿到了,这令人羞惭。我羞愧倒不怎么因为事实是就此向满世界确证了我家贫穷,而是因为自己暗地里确信,似乎“上面”所有人,亦即生杀予夺者对我不怀好意。我绝不会期待“上面”有此善意。显然,我获益于家父这个不难相处的好人的良好声望。我觉得自己与他迥异,其实,我对自己有两种相悖的看法,头号人格把我视为不甚讨人喜欢、天资平平的年轻人,雄心勃勃,禀性放荡不羁,举止让人心生疑窦,忽而天真地充满热忱,时而孩子般地感到失望,本质上是个避世的阴郁者。二号人格把头号人格看成困难而费力不讨好的道德使命,看成有待用功攻读的课程,使它难上加难的是一系列过错,如偶尔犯懒,意志消沉,抑郁寡欢,不明智地热衷于无人欣赏的理念和事物,自以为有人缘,头脑狭隘,有先入之见,(数学上!)愚蠢,对他人缺乏理解,在世界观方面含混不清,既非基督徒亦非别的什么。二号人格根本不是性格,而是尘封的生活,出生、活着、死去,一言以蔽之,是人类天性自身的全面展示;虽然无情地清楚自己的情况,就算充满渴望,却也无力,也不怎么愿意经过头号人格这一密不透风且捉摸不透的媒介做自我表达。若二号人格占优,则头号人格寓于其中并遭扬弃,正如反之,头号人格把对方视作幽暗的内心王国。二号人格觉得可以把它自己表现为一块石头,从世界边缘抛出,无声无息地沉入无尽的夜色。在它(二号人格)自身之中,却充满亮光,如在一座王宫的宽敞室内,王宫的高大窗户打开,对着沐浴在阳光中的景色。此处充满意义和历史连续性,与头号人格生活胡乱的偶然性截然对立,头号人格生活在二号人格近旁其实找不到共同点。二号人格则觉得自己与中世纪暗合,化身为浮士德,是流逝时代的遗赠,歌德显然极受他感动,对他而言,二号人格也是现实,这对我是巨大的慰藉。我有几分惊恐地预感到,浮士德对我的意义多于自己所喜爱的约翰福音,在他身上存在着我可以感同身受之事。约翰所说的基督与我格格不入,但更加格格不入的是同观福音[5]中的救世主。浮士德则与二号人格生动对应,使人坚信,他就是歌德对当时的疑问所给出的答案。这一认识不仅令我宽慰,而且也使人内心更加自信,更有把握归属人类社会。我不再是独一无二者,不再只是怪胎、仿佛天性残暴的畸形儿。我的教父兼担保人是伟大的歌德本人。
然而,起初的心领神会在此打住了,虽然我很赞赏,还是批评浮士德的结局。轻率低估梅菲斯特伤了我的心,同样如此的还有浮士德恬不知耻的居高自傲,特别是对腓利门和巴乌西斯的谋杀。
在这段时间里,我做了一个难忘的梦,让人既吃惊又振奋。那是地点不详的夜,我顶着强劲的暴风只能费力前行,何况浓雾弥漫。我拿着一盏小灯,用双手护着,它恐怕随时会熄灭。但一切都取决于我让这小灯长明不灭。我忽觉有什么尾随,回头看去,看见身后起来一个巨大的黑影。就在同一刻,我虽然惊恐,还是意识到,自己必须不顾一切危险,保全我的小灯安然无恙地度过黑夜与风暴。我醒来时,马上明白了,那是“布罗肯峰幻象”,是我自己的影子投在涡旋的雾团上,起因是我前面的小灯。我也知道,小灯是自己的意识,是自己仅有的灯。我的认识是自己拥有的唯一最大的财富,虽然无限微小,与黑暗势力相比脆弱易碎,但的确还是灯,我唯一的灯。
此梦对我意味着大彻大悟,现在知道,头号人格是掌灯人,二号人格如影随形。我的任务是护持灯盏,而不是回顾尘封的生活,尘封的生活看来是我所禁入的另一种光线王国。我不得不顶着试图遏制我的风暴,前进至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那里看不见什么,觉察不到什么是深奥难测的秘密表层。我不得不以头号人格向前,上大学,赚钱,仰人鼻息,卷入纠葛,杂乱无章,迷糊犯错,屈服,受挫。向我逼来的风暴是时间,它不停地流入往昔,却令人觉得它同样不停地紧紧尾随,它是强力漩涡,贪婪地吸入一切存在者,只有急于前行者才须臾避开。往昔无比真实,就在眼前,抓住每个不能用合格答案来自赎的人。
当时,我的世界观又经历了几次90度翻转,我认识到,自己的道路不可逆转地通往外部,通向有限、幽暗的三维。我觉得,似乎亚当从前以此方式离开伊甸园,对他而言,伊甸园成了幽灵,在他满头大汗耕种坚硬如石的农田的地方,一片明亮。
我当时自问:“此类梦境从何而来?”到那时为止,我曾以为此类梦不言自明是上帝送来的。但现在,我吸收了如此多的认识批判,就起了疑心。比如可以说我的认识慢慢有了发展,于是突然在梦中有了突破,显然,情况也是如此。但这并非解释,而只是描写。因为真正的问题是,为何发生此过程,为何它突入意识。我的确不曾有意识地做什么来支持这种发展,我赞同的对象在另一方面。幕后必定有什么在活动,是睿智之事,无论如何比我睿智;因为我不会产生那种天才的想法,即内心的光明王国在意识的眼中是巨大的阴影。现在我一下子理解许多以前无法解释的事,每次我暗指让人想起内心王国之事,诧异感与陌生感那个冷漠的阴影就落到人身上。
我很清楚,必须胜过老二,但绝不能否认它,甚至宣布它无效,这会是自残,再说那样也就根本不可能解释梦的来历了。对我而言,老二无疑与梦的产生有点关系,这需要较高智力,可以相信它具备这点。我自己觉得与老大愈益同一,而得到证明的是,这种状况只是规模大得多的老二的一部分,正是出于此原因,我觉得再也不可能与老二同一了。老二其实是个“幽灵”,亦即与暗界势力不相上下的精灵,这点我从前不知,回顾起来,可以确定,虽然感觉上无可辩驳地意识到了,当时对此事也不甚了了。
无论如何,自我在我和老二之间完成了切割,把我分派给老大,按相同比例把我与老二分隔。老二至少隐约成为某种程度上的独立人格,我不把它与对特定个性者的想象联系起来,如对幽灵的想象。虽则我出自乡野,绝对可以接受此类可能性,因为在乡间,有人相信这些事,视情况而定,信则有,不信则无。
这种精灵的唯一明确之处是它的历史特征、它在时间中的延伸或者无时性。然而,我心里没有多言此事,也不想象它存在于空间中。在我的生活背景中,这种精灵所起的作用是未及详细界定,却确定存在的因素。
人来到世上,躯体和精神上具有与众不同的素质,先了解父母的社会环境和这种环境的精神,因个性所致,人只在一定条件下与这种精神相吻合。家庭的精神又深受多数人无知无觉的时代精神本身的烙印。若这种家庭精神构成全体共识(consensus omnium),则意味着天下太平;但若它与许多人对立并且自身受挫,则会产生世无宁日的感觉。儿童对成人所说的话的反应远少于对周围环境中难以逆料之事的反应,儿童不知不觉地适应后者,即身上产生具有补偿性质的相关联系。幼儿时代袭来的奇怪“宗教”想象是自发产物,可以理解成我对父母的环境所做的反应。家父后来会明显怀疑信仰,在他身上当然有漫长的酝酿期。自身的世界,还有大千世界的此类变革早就露出先兆,而且因为意识绝望地抗拒它的威力,时间就更久了。可以理解,预感让家父不安,自然而然转到我身上。
我从未感觉此类影响出自家母,因为她不知怎么地锚定于深不见底的海底,但我从未觉得它是坚信基督教,我感觉它与动物、树木、山脉、草地、水流有点关系,奇怪的是,以此可以断定她的基督教外表下有着传统的信仰表现。这种背景符合我自己的态度,没有令人不安;相反,这种感知始终给人以安全感,让我坚信此处有坚实的立足之地,从未想到这种奠基多么“不合教义”。在父亲的传统跟我的无意识所激发的奇异补偿性产物之间,冲突初现端倪,家母的二号人格是我最有力的依靠。
回顾起来,我看出童年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预演了将来的事件,准备了适应方法,既用于应对家父在宗教信仰上崩溃,也用于令人震惊地领悟到自己如今的世界观,这种领悟确也并非旦夕产生,而是早就露出朕兆。虽则我们人类有自己的个人生活,不过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集体精神的代表、牺牲品和促进者,集体精神寿命意味着成百上千年。我们大概可以终生以为听从自己的头脑,从未发现我们基本上是世界大舞台场景中的龙套。有的事实我们虽然不了解,但它们还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因为不知不觉,影响更甚。
至少我们的一部分天性生活于成百上千年中,我私底下称它为老二,它并非与众不同的怪胎,我们西方的宗教做了证明,我们的宗教明确面向这种内在的人,近两千年来认真尝试过让表层意识及其人格主义了解这种内在的人:“别向外走,真理寓于内在的人之中(Noli foras ire, in interiore homine habitat veritas)!”
1892年至1894年,我与家父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辩论。他在格丁根市埃瓦尔德门下学习过中近东语言,博士论文写的是《雅歌》的一个阿拉伯文版本。他的英雄时代随着大学的毕业考试而结束,随后,他就忘却了自己的哲学天赋。他在莱茵瀑布旁边劳芬宫担任乡间牧师,沉醉于热情,沉迷于回忆大学时光,依旧抽着长长的学生烟斗,婚姻失意。他行善颇多,太多了,所以通常情绪恶劣,持续易怒。双亲费尽心力要过笃信宗教的生活,结果只是频繁起争执。可以理解,后来他的信仰也因该困境而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