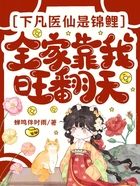
第5章 再穷不能穷教育
一夜无眠。
第二天鸡叫头遍,天还是一片蒙蒙的青灰色,沈家房的灯就亮了。
沈老头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压低了声音,神情严肃:“老大,老二,老三,都听好了。背上你们的背篓,带上镰刀,就跟往常一样,上山。记着,就说是去采蘑菇,听见没?”
沈家三兄弟对视一眼,心里跟明镜似的,齐齐点头:“爹,我们省得。”
这出戏,必须得做全套。
很快,在村里人陆续早起下地的时候,就看到沈家三兄弟背着空背篓,精神抖擞地往后山走去。
“哟,景行兄弟,这么早上山啊?”有早起的村民扛着锄头打招呼。
沈景行憨厚一笑,拍了拍背篓:“这两天下了雨,寻思着山里蘑菇多,去给家里孩子解解馋。”
这理由合情合理,谁也没多想。
直到日上三竿,沈家三兄弟才从山上下来。与上山时的轻松不同,回来时,三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狂喜和紧张,脚步匆匆,恨不得一步迈回家门。
眼尖的村里人早就瞧见了不对劲,尤其是沈守正怀里,用一件破布衣裳小心翼翼裹着个什么东西,鼓鼓囊囊的。
“守正,你们这是……采着啥宝贝了?”有人好奇地凑上来问。
沈守正脚步一顿,脸上挤出一个有些僵硬的笑容:“没啥,就,就运气好,挖了根山药。”
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不信。谁家山药用得着三兄弟一起抬下山,还跟护着眼珠子似的?
“我看不像山药,倒像是……人参?”一个见多识广的老人眯着眼,使劲嗅了嗅空气中若有若无的香气,脸色微微一变。
“人参?!”
这话一出,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村里过世的刘太爷,年轻时就曾在这后山采到过一株半斤重的人参,卖了足足四十多两银子,盖了青砖大瓦房,风光了好一阵子。可惜他家后辈不争气,没几年就把家底败光了。
难道沈家也走了这等好运?
一时间,羡慕的、嫉妒的、看热闹的目光,齐刷刷地钉在了沈家三兄弟身上。
三兄弟不敢多留,几乎是小跑着回了家,“砰”地一声关上了院门,将所有探究的目光隔绝在外。
草草吃过午饭,沈老头让沈景行和沈守正两兄弟套上牛车,将那大人参用厚厚的布料裹了七八层,藏在车斗最底下,赶往县城。
县城里最大的药铺,叫“易圣堂”,百年老字号。
兄弟俩揣着忐忑的心,抱着那巨大的人参走进去。起初,那穿着绸缎的掌柜还爱答不理,可当那布包被层层揭开,露出那根紫光莹莹、形态酷似人形的巨参时,掌柜的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
他“霍”地一下从柜台后站起来,失手打翻了茶盏也顾不上,几步冲上前,戴上老花镜,哆哆嗦嗦地凑近了看,嘴里念念有词:“紫……紫参!这品相,这根须……天爷啊!怕不是有千年了!”
最终,经过掌柜和几位坐堂老药师的再三鉴定,这株品相、年份、药性都堪称极品的紫参,易圣堂给出了一个让沈家兄弟俩当场懵掉的价格——一百八十两白银!
二百两!
沉甸甸的银子交到手上时,沈景行和沈守正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快要停了。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兄弟俩不敢在县城多待,几乎是同手同脚地爬上牛车,火急火燎地往家赶。
等他们回到家,天已经黑透了。
一家人连晚饭都顾不上吃,齐刷刷地聚在上房堂屋。当沈守正将那包沉甸甸的银子倒在八仙桌上时,那一片晃眼的白光,和银锭子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声响,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老天爷……”孙氏和付氏捂住了嘴,眼眶瞬间就红了。她们嫁到沈家这么多年,跟着丈夫勤勤恳恳,却从未想过有一天能见到如此巨款。
还是赵氏最先回过神,她看了一眼桌上的银子,又看了看自己三个同样激动得满脸通红的儿子,笑了。她先是将其中二十两银子分成了三份,推到三个儿媳面前:“老大媳妇,老二媳妇,老三家的,这钱你们各房拿去,添几件衣裳,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别省着。”
三房人谁也没推辞,她们知道,这是婆婆的一片心意,也是对她们这些年辛苦操持的肯定。
剩下的钱,赵氏拍板:“念安的满月酒,必须大办!要让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沈家有了金疙瘩!剩下的,留出老三去府城赶考的盘缠,其余的……”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窗外探头探脑的七个孙子,声音陡然拔高,掷地有声:“其余的,都拿去给孩子们念书!一个都不能少!全都送去学堂!”
沈老头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接话道:“你娘说得对!咱老沈家祖祖辈輩都是泥腿子,到了我们这一辈,好不容易出了三个读书人。如今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供孩子们念书!老三,明儿个你就带着孩子们,去你岳丈那儿,把这事给定了!”
杨氏的父亲杨老秀才,年轻时也是远近闻名的才子,只可惜时运不济,屡试不第,心灰意冷之下,便在镇上开了间私塾,教孩子们启蒙。沈家大房的沈朝云和二房的沈文振,原本就在那里念书。
第二天,沈景行便领着几个侄子去了镇上的杨家学堂。
杨老秀挨个考校了一番,发现这些孩子虽然没正经上过学,但都被父辈们教导得很好,都有不错的底子。
他捋着胡子,满意地点点头,当即便给孩子们分了班,连束脩都没要,只说就算是给未曾谋面的小外孙女的见面礼。
沈家采到千年人参,卖了一大笔钱,还要把七个孙子全都送去上学堂的消息,几天之内就传遍了十里八乡。
一时间,沈家成了所有人议论的焦点。有真心替他们高兴的,有羡慕得眼睛发红的,自然也少不了说几句酸话的。
“嗨,不就是走了狗屎运吗?看把他们能的。”
“就是,一下子送七个娃去念书,这钱烧得慌吧!”
但更多的人,却是将这一切都归功于那个刚出生的沈家小囡囡。
“你们说,是不是沈家那个小闺女带来的福气?她一出生,又是天降祥瑞,又是挖到宝参的,这也太邪乎了。”
“可不是嘛!我看那沈家小闺女,就是个福星!”
无论外界如何议论,沈家都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和忙碌之中。
转眼就到了沈念安满月的前一天。
在县城书院念书的沈守正也特地告了假,赶了回来。
沈家早就放出话去,满月酒不收贺礼,凡是沈氏族人,不拘远近亲疏,都可以来吃席。此外,村里几户平日里交好的人家,也都请了。
为了办好这场宴席,沈家特地从镇上请了掌勺的大师傅,又请了村里几个手脚麻利的妇人婆子来帮忙,几个半大小子负责跑堂。桌椅碗筷都是从族里各家凑的,摆满了整个院子。
正日子这天,天还没亮,沈家院子里就灯火通明。
“嗷——”一声凄厉的猪叫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沈家前几日买来的那头膘肥体壮的大肥猪,被几个壮汉按在长凳上,正式宣告了它猪生的结束。
烧水、褪毛、开膛破肚……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浓郁的肉香和饭菜香,混杂着人们的欢声笑语,飘散在清晨的空气里。
襁褓中的沈念安被这热闹的动静吵醒,她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母亲杨氏温柔地为她整理着大红色的襁褓,听着院子里鼎沸的人声,小小的身体也跟着兴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