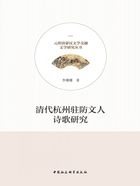
第三节 杭州驻防文学创作的先声——女性写作
目前留下诗作的杭州驻防文人中,生活在顺康雍时期的有三位,前节所述善泰诗创作于雍正年间。而另外两位是女性文人色他哈与白晓月,各存诗歌三首。她们的诗歌创作于顺治末康熙初年,开启了杭州驻防文学创作的先声。八旗女性入关后,生活环境由迁徙走向定居,家庭收入依赖旗兵饷银,与关外时期相比,家庭经济来源的单一使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下降,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庸和男性意志控制下的第二性。这与汉族女性的社会地位渐趋相似,被定位为“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59]。虽然仔细探究八旗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会发现他们与汉族女性仍具有不同,如女子不缠足、未婚及年长女性地位高等。但诗歌中呈现出来的情感与汉族女性文人并无二致。她们的心跳律动追随丈夫征战的脚步,使诗作具有了哀怨怅惘的色调。
有关白晓月是汉人还是汉军旗人尚存疑问。《国朝杭郡诗三辑》中载其“以工缣之弱质,从负弩之良人。赋命抱衾,怀伤写韵。小名三,字仙同、萼华。雅什七言,集收柳絮,若问姓名于陇右,旧事迷离,尚余记载。于城西梦魂怅惘,故重题驿壁蠖斋,亦述其诗,而远寄征衣燕客,莫稽其氏,聊存琼响。借吊珠沉乡,亲溯自钱塘,疑是白公遗胄。晓风还留残月,合增柳氏新词”[60],说明丁丙、丁申在辑录白晓月诗作时已对她的身世进行过考证,因年代较为久远,只能“疑是白公遗胄”。完颜守典《杭防诗存》“晓月”条载其“事迹无考或云顺治间汉军人白氏女”[61]。根据她为“营人某之簉室”[62]“顺治间某甲兵之妾”[63]的记载,可知她的身份是妾,推测她极有可能是汉人。因为清廷虽禁止旗民间通婚,但“所限制的,都只是正妻,对于妾,没有任何民族、门第的限制。清代旗人所纳之妾,有旗人,也有内务府奴仆,其中尤以汉人为多”[64]。白晓月丈夫去世后,正妻逼她改嫁,也侧面证明她地位低下。清初旗人所纳之妾多自汉人中抢掠而来,俞陛云《清代闺秀诗话》中就记载:“明季南都既失,江南佳丽,多被掠北行”[65]。旗兵劫掠女子,触及女性恪守的贞节观念,激发了绝命词的写作。顺治十一年(1654),湘西辰沅人,明博士员杜偕女杜小英,“为营兵所掠,立志坚贞,众莫敢犯。舟至小孤山,投江死。其尸逆流三日,浮至故居水滨,梦诉于父母。惊起迹之,获其尸,并得其怀间绝句”,诗曰:“葬入江鱼浮海去,不留羞冢在姑苏”[66],可见,清兵的嚣张气焰给传统思想世界带来的剧烈冲击,在女性写作中也引发了决绝式的生命体验与表达。
从相关记载看,白晓月与夫家不睦。白晓月、色他哈二人进行诗作唱和是缘于白晓月在康熙初年踏青半山题于庵壁上的一首诗,诗云:“万种幽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作寻常看,一字吟成千泪垂。”[67]此诗非白晓月作,而是明代会稽女子题于新嘉驿壁上的三首诗中的最后一首,因此,在她和色他哈的《重过半山次韵题壁三首》序中明言:“庚子岁主人远戍,黯然销魂,会踏青金堰,特借感同遇合之诗留题于壁。未几,色他哈来游,误认我作。”[68]按照序言所述,她因丈夫远戍而有伤怀之情,故而题壁。会稽女子的新嘉驿题壁诗的写作缘由在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八《题会稽女子诗跋》中有详细记载:“予过兖东一古驿中,见壁间有字云:‘余生长会稽,幼攻书史,年方及笄,适于燕客。嗟林下之风致,事腹负之将军。加以河东狮子,日吼数声。今早薄言往诉,逢彼之怒,鞭棰乱下,辱等奴婢。余气溢填胸,几不能起。嗟乎!余笼中人耳,死何足惜,但恐委身草莽,湮没无闻,故忍死须臾,候同类睡熟,窃至后亭,以泪和墨,题三诗于壁,并序出处。庶知音读之,悲余生之不辰,则余死且不朽。’”[69]可见,会稽女子因与丈夫不能情投意合,又受到正妻虐待,抑郁难解之下以死了之。《柳营诗传》载白晓月为“营人某之簉室,所遇不淑,抑郁之怀,常形诸吟咏”[70]。白晓月自“垂髫时,即枕席唐人诗学,含英咀华,肆力弥久”,嫁与一不通文墨的旗营甲兵,又“结缡以来,金闺独处”[71],写作的诗歌是没有知音可以欣赏的。加之正妻蛮横,相似经历使白晓月与会稽女子产生共情,以题壁诗的方式进行了“召唤式”的倾诉。会稽女子的新嘉驿题壁诗三首在明清两代引起广泛关注,诸多文人都有和作,有学者统计,明代有和者20人[72]。而白晓月的这一借用,则牵扯出一段杭州旗营内文学交融的佳话。
色他哈是旗营内“某甲兵之妻”,在白晓月题诗于庵壁之前,两人在旗营内就以“富于才,结为姊妹,时人以二乔目之,并工诗,每一诗成,互相赏析,极闺中吟咏之乐”[73]。色他哈所作《和白晓月题半山庵壁诗韵》[74]序中有:“右怨别诗,妾姊白晓月作也。初姊距妾家不数武,以故得朝夕见渠,凡有感成诗,辍以见示。妾故知其才若貌,为一时巾帼冠,虽古班谢辈弗之过也。岁戊戌姊以中秋对月作见示且索和,中有‘边塞征人意,深闺思妇情’,妾亦口号和之有‘物随秋意老,人与月同孤’句。越明年,渠良人远戍去。今年夏,妾夫、子亦从军徂闽,兰房寂寞,锦帐生寒,秋月春花,徒伴一窗萧瑟。曩者中秋对月之句,其诗谶欤?嗟乎!通于才而穷于命,丰于貌而啬于时,古今来指不胜屈。妾才若貌,固远逊姊氏,而其时命之不偶,无稍上下。今读渠壁间诗,勿禁泣数行下,因呜咽握管次原韵成三绝句。”诗云:
帐冷衾寒怨阿谁,柳烟花雨总成悲。怕看春草当窗绿,别后珠帘尽日垂。
塞外马嘶青海月,闺中人动白头悲。可怜别后庭前柳,一样黄昏带月垂。
领略春光今在谁,杜鹃声里最堪悲。香闺梦绕沙场月,曾见征人泪亦垂。
这是典型的闺怨诗,自我的思念之苦与想象中战场的寒冷寂寞形成有机联系体。别后的春光烟雨、珠帘、柳叶、黄昏,再美的景致都因少人陪伴而显得寂寥。梦中的沙场、马嘶、军帐以及边月因你的存在显得与我更亲近。其情感内涵与汉族女子写就的闺怨诗并无区别。但白晓月借用新嘉驿题壁诗表达的情感实际上超出了普通闺怨诗的范围,具有对婚姻不满的深重愁绪。因此,色他哈的和诗是误读之后加入自己情感的重新表达。时人游半山,见白晓月题壁诗,皆像色他哈一样,以为是她所作,次韵者众多。白晓月命途多舛,丈夫阵亡后,“主妇又蒙遣嫁意,犊鼻配舂,计非由己”,后主妇“疮患甚遽,家人进谀,欲邀福于神,半山祠内许长生旙愿”,因而又一次来到半山,见到色他哈次韵诗,有感而发,写下《重过半山次韵题壁三首》[75],云:
知我前生不是谁,小青又是此生悲。一书几欲央陈媪,寄谢夫人素念垂。
同境同情宁有谁,十分才地十分悲。个人欲识愁何样,两道蛾眉八字垂。
三首诗成留赠谁,有心人遇自含悲。情魂莫是东风恶,吹动飘飘裙带垂。
第一首诗有感念旗营内固山夫人之意。色他哈在见到白晓月题壁诗后,“归语其夫,遂盛传。八旗下固山夫人遣使索稿,惟恐见嗤识者,出今别离一篇上之,大为奖励。有‘江淹彩笔,独擅香奁’之评。且嘱家人看承要好,俾得雍容翰墨间与巾帼中生色,缘此满洲家姑重我能诗矣”[76]。此外,固山夫人还“常以钱米存问”[77]。可见,在清初的杭州旗营内,喜好文学的女性不在少数,固山夫人即便不能创作也懂得欣赏。男性外出征战,女性较为闲暇,则互相学习吟咏唱和。白晓月自幼习诗书,其诗歌技艺应较初入关的八旗女性高超一些,受到固山夫人爱重,也因而在家中地位稍稍得到提高。而自丈夫去世后,“主妇欲遣嫁之,晓月哭不从,主妇嫉之,禁不得与营中通问,而协领夫人亦不复晓顾其家矣。乃是年,色氏夫亦调征闽海远去”[78]。二人有着相似的愁绪,映现面庞的俱是垂落的八字愁眉,而白晓月还要面临正妻的刁难欺辱,生存境况更为凄楚。诗歌结句的“垂”字是情绪的垂丧、人生的垂萎。她们在男性的世界里忍辱负重,作为“失落了的主体”,以带有自传性质的文字留下生存的痕迹,诗作中的情感内核拥有动人心魄的魅力。
何以杭州驻防女性文学创作代替作为主体的男性文人率先留下自己的声音,这也是清初九十余年杭州驻防文人诗歌数量少的原因。首先,杭州驻防旗人初入关,自身文化基础较为薄弱,对中原文化还处在吸收学习的过程中。其次,清初东南处于战乱状态,驻守一方的杭州驻防旗人忙于战事,无闲暇时间进行诗歌创作。白晓月、色他哈二人的诗歌唱和即是以丈夫出征作为背景的。与驻防男性外出征战相反,此时驻防女性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也大都不需要为生活操劳。在关外时,男子外出征战打猎,女性大都需要从事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因此有“宁古无闲人,而女子为最”[79]的说法。再次,此时的杭州驻防男性文人不排除有诗歌创作的可能,往来征战以及调动不利于诗歌留存。毕竟两位旗营女性诗歌是以题壁诗的方式被记录下来,在开放的空间内引起读者关注,从而进行唱和,使诗作有更多留存机会。《杭防营志》载“一时名人若桐城方苞及荀梦倩辈数十人,已和之满壁矣”[80],查阅方苞集未见此和诗,荀梦倩和诗在三多《柳营谣》中有载。传唱的范围越广,人数越多,诗作留存下来的机会就越大。
同为旗营女性的白晓月与色他哈以诗作向我们展现了姊妹情深,三多云:“姊妹才情一种长,题诗先后到山墙。骚人尽解垂青眼,艳比兰芳与惠芳。”[81]荀梦倩云:“新吟为我旧吟谁,姊妹遭逢一样悲。绝胜金阊楼上女,兰芳名与惠芳垂。”[82]她们的唱和也是清初满汉文学融合的范例,谱写了一段旗营佳话。拥有较高文学素养的汉族女性进入旗营做妾,为初期满汉文学交融贡献了力量。这些为旗人做妾的汉女,“很多人在夫死之后又被再嫁与民人,她们在八旗之内出出进进,对于满汉民族间的交融,便别具了一层意义”[83]。
然而,与彼时的八旗男性文人创作的高昂情绪相比,女性诗歌则承和了汉族女性诗歌创作中的离人哀怨。在八旗制度约束、男性权力压制以及传统道德熏染的境况下,她们选择以诗歌舒展、释放自己的内心,无疑找到了一个向世人传达内心话语的绝佳途径。杭州驻防文人中的女性除白晓月与色他哈外,还有王韶、成堃、玉并、画梁、金宜等人,她们的文化素养也为杭州驻防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贡献了力量。杭州驻防女性文学创作在最初便以毫不违和的姿态进入汉族女性诗歌创作阵地,壮大了八旗女性文学创作力量,也扩展了中华女性文学创作的边界和内涵。“女性在明清时期文学发展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不论是作为文学的读者、评者、作者、流传者乃至于出版者,她们的活动其实都极为活跃与多元。”[84]诚如所言,八旗女性在创作主体及精神内核上都为女性诗歌创作注入了多元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