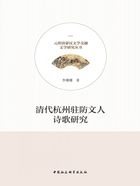
第一节 汉族文人诗笔下的杭州旗营
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通常是通过武装冲突来完成的。征服者在完成征服后,通过一系列秩序的构建,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以保证权力的实施与进行。驻防八旗的设立即是以镇守战略要地来实现由中央到地方的管控。杭州处在长江、钱塘江交汇处以及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起点,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据点。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镇压南明王朝的抵抗,在杭州“清泰、望江、候潮三门一带,悉驻兵垒”,是为杭州驻防设立之始。此时驻兵一为震慑江南社会,二为方便调动军队镇压抗清起义。旗兵被征调或阵亡使此时的杭州驻防处于“更番驻防”[2]时期,人员流动较大。顺治五年(1648),方以“江海重地,不可无重兵驻防,以资弹压。于是,下圈民屋之令”[3]。顺治七年(1650),因“旗兵与民杂处,日久颇有龃龉者”,在巡抚萧启元等人谋划下,“始定城西隅筑城以居,俾兵、民判然,不相惊扰”[4]。旗民冲突是设置驻防营的原因之一,而旗营选址又一次激化了二者的矛盾。据徐映濮《杭州驻防旗营考》载,最初总督张存仁及巡抚萧启元以杭州北部的梅家桥、水星阁等处“多场圃园囿,较为疏旷”,拟于此处建旗营,但最终清廷经“礼、工二部会议,于西城濒湖中段,圈定市街坊巷而版筑焉”[5]。杭州濒湖一带最为繁盛,将此地僻为兵营,除用水方便外,于军营的建立实为不符。西湖北南西三面均环山,旗营处于地势平坦的湖东,于作战不利。旗营选址更像是征服者的蛮横示威行为。在圈地等具体实施环节,旗兵行为更令人难以接受,“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6]。被圈民户也未进行妥善安置,迫使他们“栖止于神庙、寺观及路亭、里社中”[7],“扶老携幼,担囊负 ,或播迁郭外,或转徙他乡,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8]。杭州旗营在顺治七年(1650)建成后,又进行扩建与增筑,对杭州百姓造成相当大程度上的扰攘,从而采取由官方主导、绅民出资,以金钱换空间的方式来应对驻防八旗索求营房。[9]直至康熙八年(1669),清廷下令驻防旗兵远不得居住民房[10],此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杭人有诗《兵屯已定,故庐无恙,感赋》[11],诗题后注:割钱塘、涌金二门为满洲城,他写自己“十年临臬兀,两地总沉浮。身惯随行灶,家因逐戍楼”,书写时代乱离中个体生命的彷徨不定。而“朝廷雄镇在,是处看吴钩”“万帐穿城邑,三军逼市尘。火旗春不卷,霜角昼仍传”在对八旗军队雄健姿态的客观描写外,“逼”“不卷”“仍传”都传达出弥漫杭州的紧张氛围。接下来的“鹅眼藏金少,鱼鳞故册悬。县官严赋役,量免更何年”则以隐晦方式表达了杭州百姓的不满。鹅眼钱指劣质钱币,也代指人的吝啬,而鱼鳞册是指土地登记簿。由此结合城西百姓在被驱逐出住所后仍缴纳房税粮税二十年如故的事实,此诗的纪实性及讽刺意味就呈现出来。杭州旗营建立激起的民愤只是清初杭州城内旗民矛盾的一角,随后旗人放贷、勒索、抢劫等事件层出不穷。他们欺行霸市、凌弱老幼,加剧了旗民关系的紧张。此时的旗兵普遍文化素质较低且长期征战带有杀伐之气,在征服者身份的加持下,以及汉人持有的鄙视情绪的刺激,具有强烈的对抗心理。
,或播迁郭外,或转徙他乡,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8]。杭州旗营在顺治七年(1650)建成后,又进行扩建与增筑,对杭州百姓造成相当大程度上的扰攘,从而采取由官方主导、绅民出资,以金钱换空间的方式来应对驻防八旗索求营房。[9]直至康熙八年(1669),清廷下令驻防旗兵远不得居住民房[10],此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杭人有诗《兵屯已定,故庐无恙,感赋》[11],诗题后注:割钱塘、涌金二门为满洲城,他写自己“十年临臬兀,两地总沉浮。身惯随行灶,家因逐戍楼”,书写时代乱离中个体生命的彷徨不定。而“朝廷雄镇在,是处看吴钩”“万帐穿城邑,三军逼市尘。火旗春不卷,霜角昼仍传”在对八旗军队雄健姿态的客观描写外,“逼”“不卷”“仍传”都传达出弥漫杭州的紧张氛围。接下来的“鹅眼藏金少,鱼鳞故册悬。县官严赋役,量免更何年”则以隐晦方式表达了杭州百姓的不满。鹅眼钱指劣质钱币,也代指人的吝啬,而鱼鳞册是指土地登记簿。由此结合城西百姓在被驱逐出住所后仍缴纳房税粮税二十年如故的事实,此诗的纪实性及讽刺意味就呈现出来。杭州旗营建立激起的民愤只是清初杭州城内旗民矛盾的一角,随后旗人放贷、勒索、抢劫等事件层出不穷。他们欺行霸市、凌弱老幼,加剧了旗民关系的紧张。此时的旗兵普遍文化素质较低且长期征战带有杀伐之气,在征服者身份的加持下,以及汉人持有的鄙视情绪的刺激,具有强烈的对抗心理。
清初,杭州旗人取城西濒湖一带作为营址,导致大量居民迁出,原有的建筑被拆毁重建。旗营作为一个突发空间楔入杭州城的中心地带,改变了城市生长轴及道路网络,使原有的城市居民生活样态被打破,重塑了杭州城市空间系统。清代杭州城是由高大城墙围起来的空间,有城门供出入。旗人负责杭州各城门的关启,由此产生的盘剥勒索事件层出不穷。旗人也在西湖畔饮马放马,引发了汉城文人的集体声讨。
西湖在历代文人的吟咏中变得名声大振,成为地标性景观。从地理因素看,西湖具有的灌溉疏导功能较观赏功能对地方民生是更有益的。“湖为主,江为客;湖为清,江为浊;湖昼夜灌注,江则候有潮汐,是则防江以却其泥沙,通江以受其灌溉,固不可废。而湖之为利,尤深矣”[12],湖水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历代杭州长官大都悉心治理西湖。白堤、苏堤、杨公堤以及阮公墩都是由排淤筑堤而形成的。北方人与南方人因生活环境的差异,各自都养成了与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行为习惯。北方多山地草原而少大江大湖,多放牧而少农耕,因此,旗人固然知道水源的重要性,却不通晓水利建设。旗人营造的水道“互相排窄”,且因“所居官屋,戍满即归,非子孙授受之产,非金钱市易之券。责其从公开浚,势必苟且塞责。如锄未能豁客土,甃不及错土石,建不得高梁桥,芟不欲倾马厩。有一于此,其成将败。水之性,迅而就下;土之性,疏而善崩。必将由浅及深,因高临下。春霖秋潦,灏涣礌击,渗淫委输,不必一年,又将阻塞。阅历岁月,弊且仍前”[13]。清初驻防旗人处于流动状态,是驻防地的客居者,临时性驻扎使他们在驻地建设上应付塞责。历代杭州人为保护西湖生态,多在岸边植以桃柳、芙蓉、松柏,不只为“饰游观、追啸傲”,更为“坚堤堑、翼根基”[14],从而坚固水中泥沙保持水质清澈。而在清初“渊泉百道,久多抑没,而湖中时长阴沙,如昔所谓息壤者。隆崇崔嵬,坡陀曼衍,处处峙起。湖中三潭,昔云深不见底者,波光云影,可得俯浴。城中日暮,小儿吹角,导马出城,万蹄驰突,往往浑浊水色,腐败茭草。阅历岁月,或变桑田”[15],可见西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陈寅恪曾引汪然明写给周靖公的尺牍有:“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弟多好夜游看花……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池。昼游者尚多猬缩,欲不早归不得矣。”他后面分析说:“盖清兵入关,驻防杭州,西湖盛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独深”[16]。清初西湖的衰败自与旗人沿湖牧马、不加保护关系甚大。江南地区多丘陵河湖,本不适合牧马,马匹所吃草料也需从北方大量购进。旗人意识到这种状况,就逐渐减少了旗营马匹数量,并将牧场转移到萧山江东等地,西湖的衰败态势得到缓解。皇帝的南巡进一步恢复了西湖景观。
易代之际,本就作为书写焦点的西湖因记忆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激起文人内心的悲慨,他们或通过直观感受展现残破西湖带来的怅惘,或以梦回的方式返回繁华西湖现场进行一场充满悲情的时空之旅。尤侗《六桥泣柳记》是他时隔三十年又一次来到西湖,三十年前的西湖是诗中“晴光潋滟”“雨色空蒙”,是画中的柳浪莺闻、花港观鱼,是梦中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又一次相见则“兴尽而返。所见不逮所闻,则与其在目中,反不若诗中情、画中景、梦中人哉”。这次探访让尤侗最为痛心的是西湖的柳树,“今乃为官军斫伐都尽,千丝万絮,无一存者。荒草之中,断根偃卧而已。遥望湖心亭,倾欹几欲坠水,四围台榭,半就湮芜。昔之锦缆牙樯,香车宝马,紫箫公子,红粉佳人,不知化为何物?眼前所见,唯有寒鸦几点,梳掠斜阳,征鸿数行,哀鸣孤渚”,而除去柳树其余景象都可尽快复原,唯有“数十年之杨柳,一旦伐之,风流倾尽,为可痛也!虽使今日即树,不更阅十年,欲睹其长条依旧,岂可得哉”[17]。无复昔容的景色和无法返回的故国增添了他内心的呜咽感,继而以文字记载下返回现场的马嵬魂断、红颜憔悴的哀戚。钱谦益于顺治七年(1650)去往浙江金华,游说策反金华总兵马进宝,无功而返,东归经过杭州,目睹西湖遭受战乱蹂躏的景象,写下《西湖杂感》[18]二十首。他在诗序中慨叹“旧梦依然,新吾安往”“嗟地是而人非,忍凭今而吊古”,诗作在现实与记忆的对照中行进,充斥着个体命运携带的变节之苦与亡国之痛。“板荡凄凉忍再闻,烟峦如赭水如焚”(其一);“鹰毛占断听莺树,马矢平填放鹤台”(其三);“鹦鹉改言从靺鞨,猕猴换舞学高丽”(其九);“匼匝湖山锦绣窠,腥风杀气入偏多”(其十一),用尖锐激愤的词汇表达清兵的残暴。他在诗中营造一种凄厉的氛围,如“地戛龙吟翻水窟,天回电笑闪湖光”(其六);“罗刹江边人饲虎,女儿山下鬼啼莺”(其十五),在夸张隐喻的笔触之下也许隐含的不只是对清兵的恨意,更是对自己经历的悔恨,从而在诗作中展现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之渊的快感。朱观光为清初浙江海宁人,肆力于经学,被举荐博学鸿词科,力辞不入,有《西湖杂咏》诗云:“表忠祠畔柳毶毶,霸业犹余古剑潭。不信弩强潮可退,更无一矢射朱三”[19],含有对故国难以割舍的情愫和对八旗以武力取天下的不屑。张岱是由明入清的文人,其小品文集《西湖梦寻》以梦中返回的方式重新构建了西湖景观,带有对清初西湖景观的逃避式表达和挥之不去故国情思。“回忆具有根据个人的回忆动机来构建过去的力量,因为它能摆脱我们所继承的经验世界的强制干扰,在‘创造’诗的世界的诗的艺术里,回忆就成了最优模式。”[20]他于顺治十一年(1654)、十四年(1657)返回现实中的西湖,发现故居已成瓦砾,其“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断桥一带“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因而“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21],情辞之哀婉无助令人悲叹。西湖的残山剩水带给他极大的震撼,其中蕴藉的黍离之悲更是无法承受的重量。因此,张岱选择回到梦中去封存记忆,在灯烛下的劫后,他与似是家园眷属一般的梦里西湖四目相对,一往情深,留下千古绝唱。八旗的强权与武力纵然能破坏汉族文人心中的圣地,但却夺不走他们的情感与记忆。
而旗营作为紧邻西湖的独立空间,也在汉城文人笔下的西湖书写中以具象的形态出现,在鸟语花香、微风细雨的秀丽景色中注入猎马健儿的号角,平添了几许异质色彩。“钱塘门外水平湖,饮马健儿马上呼。打仗西山今日去,掠钱同醉酒家胡”[22],对清初旗人的张扬姿态及恶劣行径予以记载,带有讽刺意味。“路转西冷听马嘶”[23]、“猎骑嘶从黄鸟路”[24]、“钱塘门旁满州城,出到湖头眼乍明”[25]等诗句都表明清初满汉民族矛盾固然激烈,但旗营已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汉城文人诗歌书写中,作为西湖的特异部分呈现出来。“日暮军营出健儿,窄衫袒臂走离披。横担鸟铳双环眼,野鸭鸬鹚那得知”[26],通过旗人装束、打猎工具这些在江南人眼中具有陌生化特点的符号,在视觉、感官上强化了旗民间的不同。乍浦驻防在雍正年间设立,是为水师营。汉族文人诗笔下乍浦驻防具有明显的军事特点,如“雉堞参差枕海邦,移从崇德建麾幢。十家营外寻常燕,飞入三旗队队双”[27]。旗人为汉城文人诗歌注入了异质力量。
顺康雍时期,杭州旗营因选址圈地以及旗人对民人的勒索掠夺引动了民族间的对立冲突。在文人社会中,旗人以异族入主再加上对湖山胜地的污染,令汉族文人在诗文中感慨黍离之悲的同时也悲痛家园的失落,民族情感隐匿在字里行间。而即使汉族文人对旗人有着强烈的排斥情绪,旗营也开始以反面的、令人惊异的形象进入他们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