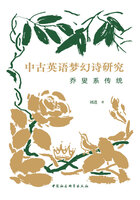
第4章 《乔叟系梦幻诗传统的开端——<丘比特之书>[25]》:作者其人
著名的中世纪学家刘易斯在其名动一时的专著《爱情寓言》(The Allegory of Love)中曾有个很有意思的“断言”:“或许,在英国早期诗人当中,写作《坎特伯雷故事》的乔叟是最当不起‘英语诗歌之父’这一称谓的了。”[26]不过,刘易斯并非要剥夺乔叟“英语诗歌之父”的美名,而是想强调,在乔叟的作品中,对于乔叟时代及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坎特伯雷故事》,而是他的译作《玫瑰传奇》,梦幻诗作《公爵夫人书》《声誉之宫》《百鸟议会》《〈贞女传奇〉序言》,浪漫传奇《特洛伊勒斯与克瑞西达》《骑士的故事》以及一些短诗,如《马尔斯怨歌》和《致罗莎蒙德》等。乔叟的追随者们就这些诗歌反复参详,从中挖掘主题细节、借鉴修辞手法、寻章摘句、竞相模仿,创作出一批主题、风格相近的作品,形成了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乔叟系传统”,囊括了英格兰诗人约翰·利德盖特、汤姆斯·霍克利夫、斯蒂芬·霍斯、约翰·斯凯尔顿等与苏格兰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和诗人罗伯特·亨利森、威廉·邓巴、盖文·道格拉斯等,也包含一些佚名诗作,如《花与叶》《淑女集会》《淑女之岛》《爱情朝堂》等。创作于14世纪末期的《丘比特之书》(又名《布谷鸟与夜莺》)采用了乔叟最喜欢的梦幻叙事框架,结合辩论诗传统抒写爱情,从文字和内容上紧密呼应《百鸟议会》《骑士的故事》《〈贞女传奇〉序言》等,被认为是“所有‘乔叟系’诗作中最早的一首,也是其中最好的一首”[27]。
关于《丘比特之书》一诗的作者,学界一度颇有争议,曾经提出了约翰·克兰沃爵士(沃德提到两位同名的约翰·克兰沃[28])、汤姆斯·克兰沃爵士(Sir Thomas Clanvowe)、理查德·鲁斯爵士(Sir Richard Roos)等可能。在现存的五个包含《丘比特之书》的手抄本中,剑桥大学图书馆手抄本(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Ms.Ff.1.6.)抄录的该诗结尾处有“克兰沃完结”的字样,基于此,学者们渐渐将范围缩小到两位叫“克兰沃”的人士:与乔叟同时代的约翰·克兰沃爵士和晚些时候的汤姆斯·克兰沃爵士。[29]斯基特(Skeat)、布鲁森多夫(Brusendorff)认为作者是汤姆斯·克兰沃,基特里奇(Kittrege)和斯卡特古德等则认为约翰·克兰沃爵士才是《丘比特之书》的作者。在斯卡特古德强有力的论证之后,[30]虽然关于《丘比特之书》作者的论争并未彻底尘埃落定,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接受约翰·克兰沃爵士为诗歌作者。[31]
约翰·克兰沃爵士(1341—1391)是乔叟的同龄人,属于德里克·珀索尔和保罗·斯特罗姆(Strohm)都曾提到的“乔叟圈子”(the Chaucer circle)。[32]乔叟的“圈中人”主要包括一些效力于王宫或担任政府职务的骑士,他们“与乔叟背景相同,在职业生涯之外也十分看重学术,当时充满活力和机遇的社会使他们从卑微的小资出身跻身于政治和思想活动的中心”[33]。这其中最显赫的一群人是“罗拉德七骑士”,即路易斯·克利福德(Lewis Clifford)、理查德·斯图里(Richard Sturry)、托马斯·拉蒂莫(Thomas Latimer)、威廉·内维尔、约翰·克兰沃、约翰·蒙塔古(John Montagu)和约翰·奇恩(John Cheyne),他们的名字时常出现在当时的历史记录中,并往往和乔叟的名字同时出现。[34]这其中,蒙塔古自己就是诗人,在法国颇受认可,尤其得到克里斯蒂·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的高度认可;[35]克利福德虽然并未亲身创作,却是“诗人之友”[36]。他与当时的法国诗人德尚来往密切,德尚那首将乔叟誉为“伟大的翻译家”的诗歌就是由他转交给乔叟的,他还有可能是乔叟儿子路易斯(Lewis)的教父;此外,乔叟还曾为克利福德的女婿菲利普·德·瓦西爵士(Sir Philip de la Vache)写过一首诗《真理》(“Truth”)。斯图里曾于1377年初与乔叟一同出使法国,并与福瓦萨尔交好。[37]克兰沃是1380年乔叟被控强奸后被释放一案的证人之一,与乔叟关系颇为密切。[38]克兰沃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使他有机会接受当时宫廷文学文化的影响,也有可能接触和欣赏乔叟的诗作,并将这全部的影响内化为创作的灵感和力量,最终呈现于自己的写作当中。克兰沃先祖为威尔士人,在赫里福郡和拉德诺郡都拥有田产。其父曾为赫里福郡议员,并曾在爱德华三世的宫廷担任骑士扈从。克兰沃与同期身份地位相当的很多人一样,早年参与了当时对法国的大大小小的一些战斗,而后以低级别骑士身份供职于贵族或王宫。从1373年起,他先后在爱德华三世和理查德二世宫廷效力,活跃于当时的内政、外交活动。有记录显示,他于1391年10月同内维尔一起死于康斯坦丁堡附近,据推测,他当时可能在朝圣的路上。[39]克兰沃常年在英国王室工作并时常出使法国,他应该非常熟悉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宫廷文化;作为与乔叟几乎同龄的“文化人”,他对影响乔叟的那些法国诗歌也必然耳熟能详;他与乔叟交好,想必能够时常第一时间聆听乔叟作品的“发布”,或许他们之间曾有过一些关于诗歌的讨论?作为一个也想在工作之余尝试写作诗歌的乔叟圈中人,他必定能更好地领会和欣赏乔叟诗歌的主题、语言和手法。克兰沃留下两部诗作,一部为宗教诗歌《两条路》(The Two Ways),另一部即《丘比特之书》。
《丘比特之书》虽短小精悍,全诗仅290行,却是一部结构完整的爱情梦幻诗,在清晰的梦前序曲—梦境—梦醒框架下通过布谷鸟和夜莺的辩论探讨了宫廷文学的重要主题—爱情。叙事者在五月这个爱情萌动的季节感受到了相思之苦,夜不能寐,辗转反侧之际想起爱徒间传言说如果听到夜莺啼鸣就会非常幸运,而如果听到布谷鸟啼叫则要倒霉,他于是决定天一亮就去林间散步,看看能否听到夜莺歌唱。清早他来到林中,在鸟语花香、流水淙淙中陷于半梦半醒状态,恍惚间听到布谷鸟啼叫,他非常恼怒并责怪布谷鸟,这时他听到夜莺在另一枝头开始歌唱。夜莺和布谷鸟就是否应该臣服于爱神展开激烈辩论。辩论过程中,夜莺伤心落泪,恳请爱神惩罚布谷鸟,仍在梦中的叙事者梦见自己捡起石头将布谷鸟赶走。夜莺向叙事者道谢,并叫他不要被布谷鸟的话迷惑,要尽心为爱神效劳。夜莺辞别叙事者,飞到鸟儿聚居的河谷中,恳请众鸟处罚布谷鸟,众鸟的代表拒绝处罚缺席的布谷鸟,提议召集一次议会,时间就在瓦伦丁节早上。夜莺对大家表示感谢,飞上枝头高歌,歌声把叙事者惊醒。这首诗完美地呈现了克兰沃对于当时宫廷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他娴熟地运用乔叟式梦幻诗框架,通过梦幻诗梦前序曲和梦境内容之间的交织、暗示与矛盾,通过对叙事者的塑造,赋予一场看似一边倒的爱情辩论微妙的复杂性,于不露声色间呈现了克兰沃对爱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