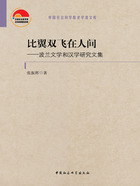
《亚当·密茨凯维奇书信选》中译者前言
波兰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的一生不仅创作了一系列波兰文学史上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的经典,如长篇叙事诗《塔杜施先生》和诗剧《先人祭》等,而且他也将他一生的精力,甚至他的生命都献给了波兰从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压迫下获得自由和解放的伟大斗争。他的书信在波兰长期以来都保存得非常完整,由华沙读者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的《亚当·密茨凯维奇全集》中有三卷是他的书信,收集了他一辈子的书信1100多封。密茨凯维奇一生的经历十分坎坷,由于他把全部智慧和精力投入了他为之奋斗的波兰民族解放事业以及他对他的亲友和同志的关心和热爱,所以他不论在什么地方居住和工作,都给他的亲友甚至他所在的地方的政府机关写了很多信,这些书信有的表示他对他的亲友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真挚的爱;有的表现了他在欧洲其他地方侨居或流浪期间对故乡的思念;有的反映了他一生文学创作的状况和他对外国文学、哲学或历史著作的翻译,对斯拉夫语言的研究,以及他对他所见到和他同时期的波兰或西方一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的评价;有的反映了他曾经在瑞士和巴黎的大学里讲拉丁文学和斯拉夫文学的各种感受。此外还有许多书信都集中地反映了他为完成投身的波兰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在不同时期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很系统和详尽地记载了他一生极为复杂的经历。我在这里选译了密茨凯维奇的书信176封,并对它们的内容做了丰富且详细的注解,这些书信都是密茨凯维奇具有代表性的,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位伟大诗人辉煌的人生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年12月24日生于立陶宛诺伏格鲁德克城郊查奥希村一个小贵族家庭。他的父亲米科瓦伊于1794年在波兰民族英雄塔杜施·科希秋什科(1746—1817)领导的抗俄民族起义爆发期间,参加过革命诗人雅库布·雅辛斯基(1759—1794)领导的起义斗争,母亲是一个地主管家的女儿。密茨凯维奇在中学学习期间,就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开始写诗。1815年中学毕业后离开家乡,他来到立陶宛的首府维尔诺,考进了维尔诺大学数理系,可是他对物理和数学没有兴趣,于是第二年春天转入了该校历史和语言文学系。密茨凯维奇在维尔诺大学学习期间,波兰各地出现了许多反抗沙皇统冶、争取民族独立的秘密革命组织。维尔诺大学当时也是一个大学生秘密活动的中心。密茨凯维奇当时常参加学校里的社交活动,1817年9月,他和他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学习爱好者会社”,简称“爱学社”,这个社团成立之初,只是为了社员之间在学习上互相帮助。1819年,在它的章程中便规定了要关心“民族的事业”,通过“发展民族的教育为祖国谋福利”,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密茨凯维奇当时除了参加这个社团在青年中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之外,他仍继续他的文学创作。他这时期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撰写文学评论文章、创作散文和诗歌等。密茨凯维奇早期的文学作品一开始就充满了对旧世界的批判,它们塑造的英雄人物表现了革命战斗的精神,闪耀着理想的光辉。
1819年,密茨凯维奇在维尔诺大学毕业后,暑假来到了他的故乡诺伏格鲁德克的一个叫杜哈诺维奇的贵族庄园,在那里遇见了一个贵族小姐玛蕾娜·维列什恰库芙娜,两人曾一见钟情。随后在这一年9月初,他在维尔诺大学又领到了在一个中学任教的委任书,来到了立陶宛的一个小镇考乌纳斯,在这里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但是他这时期和维尔诺的“爱学社”的战友们仍有密切的联系。1820年暑假期间,密茨凯维奇又回到他的故乡诺伏格鲁德克,见到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样,过去的亲友现在有的不在了,有的变得都认不出来了,感到无限的悲哀,因此他在1821年7月25日写给他的友人、“爱学社”的社员扬·切乔特的信中说:“我一离开维尔诺,就马上感到不应该离开那里。我一路上都感到非常寂寞和孤单,当我走进一栋过去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别人的房子里后,便在那曾经是我们的院子里跑来跑去。我心中的感伤使我不忍去看那空空如也的四周,我们以前住过的那一间厢房的门是开着的,但里面一片漆黑,你可以到我这里来看看。我在这里什么人也没有见到,也听不到过去那种‘亚当!亚当!’的叫唤声。这种痛苦层层叠叠地压在我的心上,使得我长时间透不过气来。我走遍了房子里所有的角落,可是当我打开仓库的大门时,突然见到我们过去的那个女仆从上面走下来了,在黑暗中只看见了她一个模模糊糊的身影,她是那么苍白,看起来非常穷困,我真是很难把她认出来。经过互相呼唤了一声才认出了她,这时我们都哭了。这个女仆曾长年住在我们这里,靠劳动养活自己,现在她生活无着落,仍不得不在这里栖身,也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这里转来转去。我身上如果有最后一个格罗什,都是要给她的。”密茨凯维奇这时又从鲁达来到了杜哈诺维奇,他在这个庄院的大门前就见到了不久前还爱过的那个贵族小姐玛蕾娜·维列什恰库芙娜,但是她因为出身高贵,不能和密茨凯维奇这么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中学教师结合,密茨凯维奇看见她后,非常感慨地说:“她坐在一辆马车上,我马上认出了她,实际上是感觉到了她就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之间已经错过了,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一张白纸。我不敢去呼叫,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我要想想,我过去是怎么见到她的?我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栋房子已经是另外一个样了,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不知道,它的壁炉在哪里?钢琴在哪里?”
但在这一时期,“爱学社”由于密茨凯维奇的倡导,后在立陶宛的格罗德诺、克列明涅茨、沃伦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也建立了秘密组织。由于它的“为民族谋福利”的社会活动在波兰影响很大,要求参加该社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在1820年秋天,维尔诺大学的青年学生又成立一个叫“爱德社”的秘密组织,它和“爱学社”具有同样的性质。1822年,密茨凯维奇在领导他的“爱学社”和“爱德社”的各种秘密活动的同时,又创作、整理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这部诗集收进了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创作的《歌谣和传奇》。随后在1823年4月他又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包括长诗《格拉任娜》和诗剧《先人祭》的第二部和第四部。
19世纪20年代初,欧洲和俄国革命走向高潮,沙俄专制主义者却充当了欧洲宪兵的角色,他们不仅镇压俄国国内秘密组织的革命活动,也开始对立陶宛的秘密组织进行搜捕,“爱德社”由于被人供出了他们的活动情况,致使包括密茨凯维奇在内的“爱德社”和“爱学社”一百多个成员遭到逮捕。密茨凯维奇于1824年10月22日被判流放俄国。这一年11月8日,他和几个和他一样被流放到俄国的战友来到了彼得堡。翌年一二月间,经沙皇政府同意,他去了南方的敖德萨,在这里的风景区克里米亚的旅游中,创作了一部《十四行诗集》,其中包括《爱情十四行诗》和《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克里米亚半岛风光旖旎,又曾长期在鞑靼汗国的统治下,受到土耳其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充满了异国情调,是浪漫主义诗人向往的地方。密茨凯维奇来到克里米亚后,这里的高山、草原、悬岩、峭壁、古堡和坟茔都令他产生了无限的遐想,这一切也给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1827年1月7—19日,密茨凯维奇在莫斯科写给与他同时期的波兰著名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约阿西姆·列列维尔(1786—1861)的信中说,他在克里米亚“经受了海上暴风雨的袭击,我是那些最健康的人中的一个,因为他们不仅最有力量,而且在目睹这些十分有趣的景象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曾经踩在克里米亚石灰岩山(样子像一个古代的饭桌)的云层上,在吉拉伊[1]的沙发上睡过觉,在玫瑰节和已经过世的汗的管家下过象棋。我在小彩画中看见了东方是个什么样子”。他的《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对他在这里的种种见闻,做了绘声绘色、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描写,使它成了波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十四行诗的经典。1828年,密茨凯维奇又出版了另一部长篇叙事诗《康拉德·华伦洛德》。
1829年3月,沙皇尼古拉表示准许他离开俄国。密茨凯维奇离开俄国后,先后到过德国的汉堡、德累斯顿、魏玛,瑞士的苏黎世、洛桑、日内瓦,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托斯卡纳和罗马等地;并曾长期居住在法国的巴黎,这是1830年在华沙爆发的波兰抗俄民族起义失败后,大批波兰爱国者流亡国外最集中的地方。1834年,密茨凯维奇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长篇叙事诗《塔杜施先生》,关于这部长诗的创作他在给亲友的信中,也曾多次提到,如他在1833年5月底写给同时期的著名诗人尤利扬·乌尔森·涅姆采维奇(1757—1841)的信中说:“我正在写一部农村题材的长诗,希望保持对我们过去那些风俗习惯的记忆,描绘出一幅我们的乡村生活,狩猎、游戏、打仗、袭击等的图画。故事情节发生在立陶宛,大概在1812年,那个时候还有许多古代的传说,还可见到过去乡村生活残留下来的一些习俗。”1834年4月19日在写给他的大哥弗兰齐谢克·密茨凯维奇的信中又说:“我现在正要印出来的我的一部新作写的是立陶宛,你在那里可以找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和打猎的描写,还有律师的见解等。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好像回到了我们那可爱的家乡。”他在1834年2月14日写给友人安东尼·爱德华·奥迪涅茨的信中也说:“作品中最好的是对我们国家的自然风光和家庭的风俗习惯的描写。”长诗确有不少诗人家乡自然风光和美好习俗的描写,透出了诗人对故乡的思念。在这里,他想到了立陶宛茂密的森林、广袤的田野和如茵的牧场,涅曼河河水静静地流淌,他想到了立陶宛古时候的景象,真希望有什么奇迹能够把他送回故乡。还有波兰古代的民族服装、饮宴、游乐、狩猎、集会、争辩、斗殴和打仗等,其中许多场面都是诗人在波兰大波兰地区走访一些贵族庄园所见到的,有的他还亲自参加过,当然已经不限于立陶宛。所以他在作品中反映的贵族日常生活的场景非常真实,而这也是密茨凯维奇自己认为他这部长诗写得最成功的地方。
对波兰从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残酷的民族压迫下获得解放,密茨凯维奇从一开始就认为要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以暴力反抗暴力”,推翻占领者在波兰的反动统治,这是拯救波兰唯一的办法,他在1835年8月初写给和他同时期的著名诗人波赫丹·扎列斯基(1802—1886)的信中,对当时欧洲和波兰的局势发展,曾经提出五点非常重要的看法,这也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政治观点,他认为:
1.在基督教欧洲的政治建筑物中,那根支撑着整个大厦的柱子要倒下来了。
2.被所有政治上的盟友抛弃了的波兰人不得不要求获得他们本来应当有的权利,这种权利叫我们以暴力反抗暴力。因此我们的民族认为,武装起义乃是拯救两千万人的波兰的唯一的办法。
3.凭良心说,未来的时刻已在召唤我们的民族投入战斗,我们也在召唤它,它会听从自己合法政权的命令。
4.敌人的打算都会要落空。
5.议会通过的决议说明了所有占领者的政府的法令都是无效的,波兰民族不承认它们的合法性,外国人也应当明确这一点。
此后在1839年、1840年和1841年,密茨凯维奇曾先后在瑞士的洛桑大学和法国巴黎的法兰西大学讲授拉丁文学和斯拉夫学。在这些讲座中,他并没有局限于对斯拉夫各国文学的介绍,而是广泛地涉及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状况,成了一门斯拉夫学的课程。他的讲座中也提到了法国在使欧洲各民族相互接近中所起的作用,来这里听讲的大都是波兰人,此外还有法国等二十几个国家的人,就连当时流亡法国的波兰侨民中贵族集团的代表亚当·恰尔托雷斯基(1770—1861),波兰爱国者、曾参加1830年11月爆发的波兰抗俄民族起义的弗瓦迪斯瓦夫·扎姆伊斯基(1803—1868)和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这些在法国和波兰侨民中影响很大的人物,也都来听过他的课,而且对他的评价都很好。巴黎的《民族报》一次报道说:“任何一个讲座都没有这么使人感兴趣……它展示了人们至今不知道的文学宝库。”1840年年底,流亡巴黎的波兰侨民正集资买了一个价值一千零五十法郎的银杯,赠给了密茨凯维奇,碑上刻写了“亚当·密茨凯维奇,留作纪念,1840年12月25日”的字样。这一天正好是圣诞节,又是密茨凯维奇的命名日,他的友人雅努什凯维奇邀请他,以及和他同时期的波兰浪漫主义代表诗人尤利乌斯·斯沃瓦茨基(1809—1849)等37人参加一个晚宴,在宴会上,斯沃瓦茨基受与会者的委托,亲手将银杯赠给了密茨凯维奇,所以密茨凯维奇在第二天,也就是1842年12月26日在写给著名诗人波赫丹·扎列斯基的信中说:“法国人很喜欢我的课,如蒙塔仑贝尔、福谢和凯尔戈莱[2]等,他们认为,这个讲堂的设立就是作为大学里一般的讲课,也是很明智的。……昨天我们在尤斯塔切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斯沃瓦茨基在这里还即兴赋了一首诗,我也回应了一首,这是我自创作《先人祭》以来从未有过的灵感。”
最重要的是,密茨凯维奇在这个讲座上讲到了他对“祖国”这个概念的理解,他说“祖国”这个词在波兰最早的史学家加尔·阿诺尼姆(10—11世纪)用拉丁文写的《编年史》中就已出现,因此自波兰于公元966年建国以来,在波兰人中就有这个概念。密茨凯维奇认为,祖国包括波兰从古到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既表现在物质方面,也包括精神方面,爱国主义就是“要创造一个自由、幸福和强大的祖国”。对一个波兰人来说,不仅波兰是他的祖国,而且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他心系波兰,那里就有他的祖国。这当然也反映了密茨凯维奇和当时侨居国外的波兰爱国者中普遍存在的爱国思乡的心境。
1841年5月初,一个立陶宛的宗教神秘主义者安杰伊·托维扬斯基从瑞士的布鲁塞尔来到了巴黎。他原是维尔诺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年轻时就醉心于研究人性心理状况,有一套宗教神秘主义的思想观点。早在1832年他在彼得堡时,就跟密茨凯维奇的妻妹海仑娜·马列夫斯卡和她的丈夫弗兰奇谢克·马列夫斯基有接触。1835—1836年,他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又和密茨凯维奇的友人安东尼·爱德华·奥迪涅茨交往密切,因此他对密茨凯维奇和他的妻子策琳娜的情况非常了解。托维扬斯基来到巴黎后,于1841年7月30日前来拜访密茨凯维奇。这时密茨凯维奇的妻子策琳娜得了精神病,已住进精神病院。托维扬斯基假惺惺地对密茨凯维奇的不幸表示关心,他说,上帝在召唤你们,他会帮助策琳娜尽快恢复健康。托维扬斯基还要密茨凯维奇把策琳娜从医院里接回来。与此同时,他还向巴黎的波兰流亡者保证,说他们很快就可以回国,他们不幸的命运已经结束了。密茨凯维奇作为一个爱国者,这一时期的思想本来深受宗教神秘主义的影响,而这时他又看到波兰在巴黎的侨民和波兰国内的状况非常不好,如他早在1833年3月22日致诗人尤利扬·乌尔森·涅姆采维奇的信中就说:“我感到不高兴的是我现在从文学转向我们那可怜的政治了,你幸好住在伦敦,不可能从近处看到流亡者身上的伤疤和虱子,可我们的一双眼睛看到了祖国这么多的不幸,又看到我们的同胞是这个样子,的确是无法忍受的。”托维扬斯基现在这番话对他来说,当然有很大的诱惑力。因此他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紧跟托维扬斯基的脚步,不仅尊他为大师,在1842年5月初,还和托维扬斯基以及一些和他一样信奉托维扬斯基的波兰流亡者在巴黎近郊的一个农舍里开会,宣布成立一个“上帝事业集团”,同时,他在法国的楠泰尔还成立了一个叫“波兰圈”的组织。宣扬要在宗教博爱思想的指导下,实现斯拉夫和世界各民族的统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波兰民族负有特殊的使命,要通过自己受苦受难使世界各民族得到拯救。这显然是一种空想。特别是当时无论在波兰还是欧洲都存在严重的民族和阶级矛盾,这种思想宣传不论对波兰还是对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不利的。托维扬斯基这种欺骗性的神秘主义宣传也引起了法国政府的不满,1842年7月16日,他接到了法国内务部要他离开法国的命令,18日就离开巴黎到比利时去了。此后,密茨凯维奇受托维扬斯基的委托,继续领导“上帝事业集团”和“波兰圈”的活动,在波兰侨民中,后来又在法国人中发展信徒,而且要加入这个集团的信徒宣誓,忠于它的“事业”。由于他们的活动比较分散,密茨凯维奇又将集团或“波兰圈”的成员分为若干小组,每组七人,平日各个小组可以单独活动,每礼拜派一个代表开一次团会,一般由密茨凯维奇主持,平日他对各小组的活动也很关心。
但不论密茨凯维奇如何相信托维扬斯基的宗教神秘主义说教,他还是要把他的信仰和他所崇拜的拿破仑,和波兰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没有放弃对波兰民族解放事业的关心。如他1844年7月底写的一封“致审查为拿破仑建立纪念碑的图像的委员会的委员们”的信中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基督教有了新的需求,为我们这个地球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拿破仑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之火和新的追求的具体体现,将所有那些在基督教前进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人们都团结起来,朝着一个精神的目标前进。拿破仑是一个新时代的法国人,他也是一个波兰人,一个意大利人,甚至部分地是个德国人,因此他种下了各族人民新的大联合的种子。”“法兰西民族热爱拿破仑,他们都愿意跟随着他,因为他带领他们走上了一条真正的进步的道路。他的精神也是他民族的精神,这里也表现了耶稣基督的精神,是很圣洁的。拿破仑战争的胜利果实和他的精神果实既属于他,也属于法兰西。”密茨凯维奇认为,拿破仑和他的精神也就是他心目中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宗教人道主义精神,能够指引波兰民族和人民获得解放,不仅使波兰从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民族压迫下获得解放,也要使波兰人民从波兰国内的封建压迫下获得解放,如他1847年7月27日写给菲利克斯·弗罗特诺夫斯基的信中,说他的“波兰圈”里“以后还有各种要做的事,而现在我们就是要尽力保持我们这种波兰的朴实和真诚,要从那个已经灭亡的祖国,那个压制了一切最深刻感情的贵族的粗暴行为和在我们中已经根深蒂固的贵族老爷傲气的罪孽中解救出来。这个贵族老爷的傲气本是犹太人和法国人的习性,在巴黎有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兄弟啊!现在是我们在相互之间的接触中,要改变这种习性的时候了,如果能这样,说明我们有了提高,能够达到大师的要求了”。
19世纪40年代末,在全欧洲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欧洲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也使波兰的流亡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时期,密茨凯维奇也一直关心欧洲和波兰革命形势的发展,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他已经认识到要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改变旧的社会秩序,必须马上建立波兰的武装部队。当时,波兰流亡者的各派首领也一直努力要在巴黎建立波兰军团,到波兰去作战。密茨凯维奇希望教皇支持波兰在罗马建立军团,1848年3月29日,一些拥护密茨凯维奇的政治派别的人在他那里开会,决定马上建立一支波兰军队,并做出了一个政治改革的决议,内容包括把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男女平等,各阶层人民平等,在决议上签名的有14个人,这就是密茨凯维奇要建立的军团的基本队伍。1848年4月10日,他率领由11人组成的军团队伍从罗马出发,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沿途受到意大利居民的热烈欢迎。密茨凯维奇也给巴黎的《法兰西报》写文章,号召斯拉夫各民族团结起来,支援意大利,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奥地利占领者。巴黎的波兰流亡者也有一批自愿者来到佛罗伦萨,参加了密茨凯维奇的军团。后在米兰甚至受到了意大利临时政府总统的热烈欢迎,他在市政厅里发表讲话,又一次指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遭遇到了同样的民族悲剧,都在为自由而战斗,“为了人民共同的自由”,两个民族要团结起来。
他这一时期的书信有很多都反映了他正积极筹备,要在意大利建立波兰军团的事,他认为在意大利不仅要建立波兰军团,而且还要建立斯拉夫军团,和意大利人民并肩战斗,反对奥地利侵略者。1848年欧洲各国的革命最后失败,密茨凯维奇并没有对前途丧失信心,后来波兰的流亡者打算在土耳其建立一个波兰军团,这个军团的成立得到了法国国王拿破仑第三的支持,1855年夏天,英国和法国在土耳其反俄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这两个国家也同意在土耳其建立一个波兰师,9月22日,密茨凯维奇来到了土耳其,10月6日,他又去过保加利亚的布尔加斯新港,见到这里已有波兰的流亡者建立的军团,他希望在这里再建一个犹太军团,和波兰军团一起,为被瓜分和奴役的波兰获得自由而战,但11月27日,他在土耳其因染上了霍乱而死去,很遗憾没有见到他愿望的实现。密茨凯维奇不仅是波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诗人,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将他的毕生精力,甚至他的生命都献给了波兰民族的解放事业,虽然他的一生并没有看到波兰恢复国家的独立,但是他的思想和他在波兰文学史上早已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却对波兰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作为波兰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不仅在艺术上有了许多可贵的创新,而且他的作品中表现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波兰人,去为他们民族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密茨凯维奇不仅是波兰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世界各国的人民中也早就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在195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纪念他逝世一百周年,宣布他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各国人民的敬仰。
[1] 古代克里米亚汗的一个王朝的名称。
[2] 让·弗洛里亚洛·凯尔戈莱伯爵(Jan Florian hr.Kergoley,1803—1873):法国政治家,密茨凯维奇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