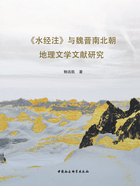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地记的山水化文学化演进
应该明确的是,地记毕竟地理著作,以记载地理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风俗物产等为主要内容。所以并非所有的地记都有很强的文学性。只是到了魏晋南北朝,特别是晋宋之际,很多地记作品中的山水描写显著地增多了,而且文笔越来越优美。这使得魏晋南北朝地记,既不同于东汉专记地理的地理书如班固《汉书·地理志》、应劭《十三州记》和《地理风俗记》等著作,又不同于唐宋以后的方志。唐宋以后的方志,关注的重心在于建置沿革,四至八到,资源物产、人口贡赋等,功用偏重于“资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却有偏文学化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地记文学色彩的加强,大概与当时王朝政治对私家撰修史志的控制的相对宽松,因而有较多的文学之士参与到地记编修的背景相关。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相仍,政权交替频繁,导致朝廷官修地理书的难度很大。《宋书》卷一一《志序》载:“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放松了对私家撰书的控制,于是文人的创作涉足于地记领域,而地记的撰著也随之渐染了文风。其时的地记作者,很多都是以文学见称的才俊之士,如谢灵运、刘义庆、吴均等。特别是晋宋以来,士人撰写地志的热情明显高涨。一方面,往往出现不同作家撰写同一地域的地记的情况,如《荆州记》,就有范汪、盛弘之、郭仲产、庾仲雍、刘澄之等六家撰写;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作家不止撰著一部地记,如刘澄之、郭仲产、庾仲雍、山谦之、王韶之等,都撰著有多部地记。一些优秀的地记作家,对山水表现出真心的喜爱,有时为保证记录的真实准确和精彩,还会登临山水,亲自考察观瞻。例如,《水经注》卷三十七《夷水》“东南过佷山县南”条注文记载:“(长杨)水源东北之风井山,回曲有异势,穴口大如盆。袁山松云:夏则风出,冬则风入,春秋分则静。余往观之,其时四月中,去穴数丈,须臾寒飘卒至,六月中,尤不可当。往人有冬过者,置笠穴中,风吸之。经月还步杨溪,得其笠,则知潜通矣。”[232]袁山松对风井山的特殊地貌做过考察,才写出了“须臾寒飘卒至,六月中,尤不可当”的神奇感受。再如,《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又东过夷陵县南”条注文曰:“袁山松言:江北多连山,登之望江南诸山,数十百重,莫识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异势,自非烟褰雨霁,不辨见此远山矣。余尝往返十许过,正可再见远峰耳。”[233]袁山松“尝往返十许过”,就是为了找到望江南诸山的感觉,可见其对山水之爱早已入目入心了。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其《廿二史考异》中曾说道:“予谓魏晋诸儒,地理之学极精。”[234]诚然如是。
一 山水审美观念在晋宋之际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山水审美文化开始崛起的时代。这首先体现在山水观念的重大转变。有学者概括说,魏晋南北朝从敬畏崇拜的宗教山水观和道德象征的哲学山水观“大飞跃”怡情畅神的审美山水观,“山水不再是神灵的寄托和道德伦理的表征,而是纯粹的娱目消忧、适性畅神的美感对象”。[235]这样的概括是简洁而准确的。
自然山水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审美的对象的。山水审美观念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早期先民生存能力有限,自然灾害的发生让他们感到惶恐,自然的神秘他们也无从解释,于是他们把自然看作有无限威力的力量而对之产生敬畏和崇拜:“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236]但是随着人与自然物质和能量交流的加深,自然的馈赠也让他们逐渐产生了愉悦的情感。但这种情感还是非常朴素的。《诗经》等先秦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关于山水地理的语句,虽然还都只作为叙事与描写的背景出现的,但可以证明山水已经引起人们朦胧的关注,也说明人与山水自然在情感上的拉近。一些哲人也开始把人的品德和社会伦理道德与山水自然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比如孔子的“比德说”即是代表。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237]当然孔子在这里是把山水看作道德的象征了,但其也表明自然山水与人是相亲的。自然山水给人类以生活的资源,人类没有理由不与之亲近。
魏晋以来,随着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思想文化渐趋活跃,人开始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玄学家强调自然与人的相通性:“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238]在玄学家眼里,山水是体玄的工具。如孙绰就说:“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239]试图通过对山水的体悟来领略玄理,达到心与物游、万物同化的境界。南朝宋宗炳在《画山水序》也说:“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乐乎?”[240]“山水以形媚道”,意思就是山水是顺应自然造化的产物,因其形质的美好,所以是“道”的最佳表现形式。这还是借山水来证“道”,也不是纯粹的、以怡情畅神为目的的山水审美观。
纯粹的、以怡情畅神为目的的山水审美观,实始自东晋的地记作家袁山松。《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注》还引述了袁山松《宜都记》中的一段话:
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迭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241]
这段文字尤其最后三句极可注意,它是袁山松对自己山水审美自觉的直接表现。自觉,是自觉为“山水之美”的“千古知己”。袁山松表现出了山水自然审美自觉。这种“知己观”,不但与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山水比德观畛域分明,而且与当时盛行于世的“玄对山水”的悟道观也大异其趣。
自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讲“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以后,《尚书大传》《韩诗外传》《荀子·宥坐》、董仲舒《春秋繁露·山川颂》、刘向《说苑·杂言》都极其力以润色之,皆以人类的道德观念附会于山水自然。如董仲舒《山川颂》:“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242]这是把山水看作人的精神品质的表现或象征,这是自然的拟人化。比德观属伦理学层面。
道家的山水观基于对自然之道的体认。老子讲“道法自然”[243]。魏晋玄学家们认为,天地万物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者:“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244]浏览八荒,纵观万象,山山水水莫不体现着道:“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245]于是,山水就成了蕴道的万物的代表。人也是自然之一分子,“元气陶铄,众生禀焉”[246]。“二仪陶化,人伦肇兴。”[247]因而,人可以通过与山水的心灵对话,来达成对道的体认和沟通:“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248]这种审美方式突出的重点是对于道的理解和通融,这是把人拟自然化了,其特点是玄理意味浓重。悟道观属于哲学层面。
知己观则是审美层面。袁山松以“山水之美”的“知己”来自觉、自承。他自觉地走进山水,融入山水,用身体去体验山水。他是把山水作为无功利非实用的独立审美客体去认识的。“他观赏山水景物,不再是去寻找己心与道蕴的契合,而是把自己的感情直接向山水,以感性的形式来欣赏山水之美,以纯审美方式把握山水,这不能不说是山水观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山水审美的自觉意识,遂成为山水意境的核心。这对山水文学本身的形成也具有创造性的贡献。”[249]山水文学的最大特质就是山水在视觉上成为作家的真正审美客体,在题材上成为一篇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而这是“玄对山水”的“悟道观”所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的。因为要“悟道”,诗文中即使有对山水的描写,但重心却是对“道”的理解,玄言诗中微量的山水描写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是,袁山松等则突破了这种束缚。在山水审美自觉意识的深刻作用下,山水之美的描写开始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
山水自然的审美认识,大致经历了一个理消情长的过程。老子所言之“自然”,还是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而庄子则把它努力地形象化,而且打通人与外界的隔阂,强调人与万物的会通交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正始年间,王弼注《老子》,士人们多以抱虚守静、游心太玄为旨归,理念化色彩还很强烈;至西晋,向秀注《庄子》,“发明奇趣,振起玄风”,郭象又“述而广之”,于是,玄风大炽,士人们又多以会通万物、陶铸天性为雅致,乐于把情感投射向万物,而入于凝神的境界。这样,山水就得到了人们进一步的关注。这说明,人们的山水意识已经在逐渐地从抽象化而向具体化、形象化的方向发展着。但直到袁山松叙写陶醉于山水美景的感受,才标志着由借山水以证道的传统山水观念的结束,标志着山水审美意识的新发展。他们这种全新的山水审美自觉意识和适性快意、赏心悦目的审美方式,给后来的谢灵运、郦道元以很大的启发和影响。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中明确表示:“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再看《水经注》卷三十七《夷水注》:“静夜听之,恒有清响,百鸟翔禽,哀鸣相和,巡颓浪者,不觉疲而忘归矣。”[250]这里郦道元写的,也正是陶醉于山水美景的感受,与袁山松等晋宋地记作家的审美趣味非常契合。
二 魏晋南北朝地记山水审美的经验特质
王立群在《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中曾经提及:“为什么中国的山水散文会首先由作为方志先声的晋宋地记推向成熟之巅?为什么晋宋时期的山水文比山水诗要显得有些早熟?……笔者认为,既然这些优秀的山水散文产生于晋宋地记之中,那么从探讨晋宋地记入手,应当说不失为阐释这一文学现象的一条可行之路。”[251]王立群的思路不错。我们就先从地记里的一些内容来了解一下时人对于山水自然的态度。
魏晋南北朝地记里记载时人游览自然山水以后的心情和感受的章节,委实不少。其中关于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字逸少)的记载较多。例如,南朝梁顾野王《舆地志·扬州部》: “山阴南湖,萦带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发,若镜若图。故王逸少云: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252]王羲之游览山阴南湖,深为美景陶醉,以诗句表达自己的感受说“如在镜中游”,绍兴的镜湖之名就由此而来。南朝梁吴均《入东记》写昇山:“王羲之为太守,常游践,尝昇此山,顾谓宾客曰:百年之后,谁知王逸少与诸卿游此乎!因有昇山之号,立乌亭于山上。”王羲之为官之暇,常常登临山水以为游赏。他登上昇山,感慨无限。王羲之在《兰亭序》也曾这样感慨:“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王羲之感慨的是人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尽享山水之乐,岂不是永久的憾事!
东晋王氏家族,喜好山水的很多。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写王子敬游会稽诸山:“会稽境特多名山,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摧干竦条,潭壑镜澈,清流写注。王子敬见之,曰: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253]王子敬即王献之,王羲之第七子,也是著名书法家,与其父并称“二王”。“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有两方面的意思表达,一方面是说景色太美了,让人流连;另一方面是说王献之深深地被映入眼帘的美景打动了,唯恐错过任何一个。可见喜爱的程度之深。山谦之《丹阳记》曰:“晋车骑将军王舒令其子曰:甚爱溧阳县,死则我欲葬焉。故王死之后,徙县治今处,而以昔廨为墓。”[254]王舒是丞相王导、大将军王敦的堂弟,在平定东晋初年的两场大乱中皆有助力。他由衷喜爱风光优美的溧阳县,才会产生卒葬之愿。山谦之《吴兴记》:“从溪以上至县,悉石濑恶道,不行船,以下水道无险,故行旅集焉。晋王朗之为吴兴太守,至印诸中,叹曰:非唯使人心情开涤,亦绝日月清朗。传云渚次石文似印,因以为名。”[255]王朗之,王廙次子,年少时就很有声誉,成人后更是才能卓著,颇有作为。他任职吴兴太守时经过印诸,也明确表达了自己深受山水陶冶而心情大好的感受。
非独王氏家族,东晋其他世族,也多有山水之好。山谦之《吴兴记》:“於潜县西二里,有岞崿山,有绝壁高三十许丈,谢安尝登之,临壁垂足曰:伯昏无人,何以过是?当时称以为难。一云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于此。”[256]谢安是东晋著名政治家,本有东山之志,屡与名士游山玩水。谢安登上岞崿山,为此山之高峻大感惊异,说伯昏无人也难以超过我此时的感觉了!伯昏无人是道家虚构的一个人物。《庄子·外篇·田子方》记载,列御寇射箭给伯昏无人看。伯昏无人观赏完列御寇看似无人可及的高妙箭法后,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于是伯昏无人真的登上高山,表演给列御寇看,他“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让列御寇看傻了眼,“汗流至踵”。谢安在这里是以自己来比伯昏无人。观其处变不惊的神情气度,倒是颇有伯昏无人的风采。这座山太高了,“当时称以为难”,不知叫什么名字好了。于是后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岞崿山。岞崿者,山之高峻貌也。又如南朝齐王僧虔《吴地记》载:“桐庐县东有大溪,九里注庐溪口,南通新安,东出富阳,青山绿波,连霄亘壑。昔征士散骑常侍戴勃游此,自言山水之致极也。勃字长云,谯国铚人。父散骑常侍逵,字安道。弟子常侍国子祭酒颙,并高蹈俗外,三叶肥遁,为海内所称。”[257]桐庐“青山绿波,连霄亘壑”的美景,被隐士戴勃呼为“山水之致极”。他与其父戴逵、弟戴颙,一并隐居于此。
非独南方的东晋爱山爱水,就连北方的悍将竟也为山水的壮美所折服!段龟龙《凉州记》曰:“契吴山,在县北七十里,赫连勃勃北游契吴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海。吾行地多矣,自岭已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斯之壮丽矣!”[258]赫连勃勃是十六国时期胡夏建立者,南征北战,雄霸一方。他对契吴山也是通过自己亲历山川,才做出的比较和评判。
入宋以后,徜徉于山水之乐者也不少。《新安记》:“锦沙村,傍山依壑,素波澄映,锦石舒文。冠军吴喜闻之而造焉,鼓柁游泛,弥旬忘返。叹曰:名山美石,故不虚赏,使人丧朱门之志。”[259]吴喜在宋明帝刘彧即位时平叛有功,被封为竞陵县侯。吴喜作为武人,亦有山水雅趣,看到“傍山依壑,素波澄映,锦石舒文”的锦沙村景色如此美好,流连忘返,赞叹不已。
魏晋南北朝地记里记载了这么多真心喜爱山水、把山水当作审美对象的人物,记述了他们在面对山水时由衷陶醉的感受,也就可见把山水当作知己的未必只有袁山松一人。宗白华先生说得不错:“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260]
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们从自然山水获得的印象不同,因而对于自然山水的认识也不同。我们可以把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山水的态度和先秦时期对照一下。《列子·汤问》:“太行王屋二山,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西山而居,惩出入之迂也。”愚公感觉不到二山的美,只是因为“惩出入之迂”,就决心要将它们夷平,可见何其厌恶此二山。《吕氏春秋》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亡。”写的也是洪水肆虐和人们余悸未消的恐惧。这些说明那时候人们对山水还是用功利的眼光去看待山水,当山水有碍于他们的生产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对山水产生了抵触甚至厌恶的情绪。
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人与自然交流的日益深化,当自然山水的良性馈赠越来越被人类接受的时候,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认识开始转变了。人们在与山水的关系,开始从被动、敬畏、恐惧,走向主动、融合、亲近,山水的美感色彩也就不断凸显,人们的山水审美意识就开始觉醒。正史中记载雅好山水的人物也不乏其例:
(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261]
(阮籍)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当其得意,忽忘形骸。[262]
(孙统)性好山水,乃求为鄞令,转在吴宁。居职不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263]
(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264]
(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亦尝结宇衡山。[265]
(刘凝之)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岭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妻子皆从其志。[266]
(萧统)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267]
(陆瑜)每清风朗月,美景良辰,对群山之参差,望巨波之滉漾,或玩新花,时观落叶,即听春鸟,又聆秋雁……一俱怡耳目,并留情致。[268]
由此可见,以山水为知己,是晋宋时期士人的群体心理,袁山松是这个群体中杰出的代表。袁山松的优长在于他不但能够对山川美景悠然心会,而且还能够述之以文,写下“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的感悟,从而成为山水“知己观”的最早提出者。
这种山水“知己观”,是以走进山水,躬身体验为前提的。人们与山水触目而会,心生喜悦,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说的那样——“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人们是通过自己真切的体验感受到山水是令人愉悦的存在。前述地记的例证中人物的共同特点就是:诸人都亲自投身于山水,亲自参与到山水审美的过程之中了。王羲之说“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讲的是自己在行路途中的感受;王献之说“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也是说当美景扑面而来的时候,自己的眼睛不够用了;谢安如果不登上高峻的岞崿山,恐怕也不会联想到伯昏无人的典故;郗愔也是“遍游诸境”,才卜居罗璧山。至于赫连勃勃,就直说“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壮丽矣”;褚渊也是直说“之所称,多过其实。今睹虎丘,逾于所闻”。这些人都特别强调了身体在场性的山水经验。身体在场的山水审美是调动全部感官的全身心的投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提到人是如何欣赏体验山水:“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欣赏者与山水之间有着良性的互动:自然山水作用于欣赏者,欣赏者反复地观察自然山水,从中产生实际的审美体验,内心有所抒发,这就是“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山水之美引起欣赏者写作的灵感和写作冲动,就是“情往似赠”欣赏者如果以情接物,将体验再现成文学作品,就是“兴来如答”。所以,当欣赏者把山水也作为和自己一样的生命体的时候,人与山水就建立了一种“知己”般的亲密关系,人与山水也就产生了“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交往互动。当袁山松把它用文字表述出来的时候,也就构建了山水审美的“知己观”。
三 魏晋南北朝地记山水化文学化的演进线索
袁山松提出了山水审美的“知己观”,并且以其优美精彩的文笔撰著了可以作为中国山水文形成的标识的地记名作《宜都记》。但在《宜都记》之前,还有两部地记值得注意:一是汉末辛氏所撰的《三秦记》,二是东晋早期罗含所撰的《湘中记》。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列举地理书时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269]他专门提出的四部地记作品,除了《华阳国志》以外,皆有文学色彩。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历史地理著作,实用性较强,而文采不高。盛弘之《荆州记》产生于刘宋,文学色彩最浓。辛氏《三秦记》和罗含《湘中记》,则为在地记中写景状物导夫先路。所以明代牛若麟在(崇祯)《重修吴县志序》中说,后世地记与方志的创作,都以此二书为榜样:“其叙土宇、山川,洎物产、风化,往往模拟《湘中》,斟酌《三秦》,是地理书体也。”[270]玆从此二记开始,寻绎一下魏晋南北朝地记山水化文学化的演进线索。
(一)辛氏《三秦记》的文学色彩
诸地记中,辛氏《三秦记》时代较早。《三辅黄图》、梁刘昭《后汉书·郡国志》注、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后魏郦道元《水经注》、贾思勰《齐民要术》等书,已相继采用,而且所记山川、都邑、宫室,都是秦汉时事,并不及魏晋,是知此书必汉代人所著。
《三秦记》中已经有一些对山水景物的初步描摹。如写华山:
华山在长安东三百里,不知几千仞,如半天之云。[271]
以“半天之云”喻山之高峻,显得十分新奇。晋罗含《湘中记》“遥望衡山如阵云”[272]的写法,显然系受《三秦记》启发。
《三秦记》写仇池山的险要:
仇池山上有百顷池,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东西绝壁百仞,上有数万家,一人守道,万夫莫向。山势自然有楼橹却敌之状,东西二门盘道可七百里,上有冈阜泉源。《史记》谓秦得百二之固也。[273]
寥寥数语,就把山险上平,易守难攻,“一人守道,万夫莫向”的特点刻画出来。
再如写河西沙角山:
峰岩危峻,逾於石山。其沙粒粗,有如乾糒。[274]
以乾糒喻沙,不但十分形象,而且浅显易晓。刘宋段国《沙州记》:“洮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黄沙犹若人委干糒于地,都不生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沙州于是取号焉。”[275]是继承了《三秦记》的写法。
写龙门水,《三秦记》亦状物生动:
龙门水悬船而行,两旁有山,水陆不通,龟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故云暴鳃点额龙门下。[276]
《韩愈集》卷九律诗《义鱼招张功曹》:“濡沫情虽密,登门事已辽。”登门,即谓此也。《柳宗元集》卷十四《设渔者对智伯》:“垂涎流沫,后者得食焉。然其饥也,亦返吞其后。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为螭龙。”也是化用《三秦记》此条之意。这已成为后世习用的典故。
在《三秦记》中还用一些录歌谣谚语刻画山水形象,如: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山川险阻,黄金子午。蛇盘鸟栊,执与天通。[277]
这首歌谣谚语表情达意通俗生动,三言两语便绘形传神,便于打动读者,因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也使后世文人努力效法,如范成大诗“侧足二分垂坏磴,举头一握到孤云”就是由《三秦记》“孤云两角,去天一握”点化而来。
辛氏《三秦记》已透露出山水描写的端倪,是山水散文的萌芽阶段的代表性作品。
(二)罗含《湘中记》的文学色彩
罗含字君章,《晋书》卷九十二有传。罗含与谢尚、庾亮、桓温同时,曾先后为庾亮、桓温的僚属[278]。考庾亮生于太康十年(289),卒于咸康六年(340)[279];桓温生于永嘉六年(312),卒于宁康元年(373),可知罗含生活于东晋前期。
罗含《湘中记》继承了辛氏《三秦记》的创作笔法,继续增加山水描写内容,提高山水表现技巧,在晋宋山水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功不可没。
《湘中记》有时通过释名来揭示山水的特点或位置,加强描写的情趣内容:
九疑山在营道县,与北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280]
有时用生动的比喻,突出山水的主要特征,有引人入胜之致:
衡山近望如阵云,沿湘千里,九向九背。[281]
有时利用色彩和声响加强描绘的力度:
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雪,赤岸如朝霞,绿竹生焉,上叶甚密,下疏寥,常如有风气。[282]
(衡山)山有锦石,斐然成文。衡山有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有鹤回翔其上,如舞。[283]
还有下面一则:
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284]
用夸张性比喻构成悬殊的对比,显现湘水上下游狭阔变化极大的特点,可见作者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已经有较高的造诣。
与辛氏《三秦记》比较,罗含《湘中记》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湘中记》中的山水景物描写,是作者有意为之,不再像《三秦记》多为临时性的比喻。
第二,《湘中记》中的山水景物,以清丽空灵为特征,很能体现南方地理的幽美特点;而《三秦记》则往往表现西北地理的险壮特点。
第三,《湘中记》模山范水,注意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加强表现效果,艺术表现力较《三秦记》有所提高。
第四,《湘中记》出现了一些对偶和诗句化的描写语句。明杨慎《升庵诗话》指出,出自于罗含《湘中记》的“青崖若点黛,素湍如委练”“白沙如霜雪,赤岩若朝霞”“沿庭对岳阳,修眉鉴明镜”诸句与诗句非常类似[285]。从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文字渐趋整饬化对于地记著作的影响。
罗含《湘中记》的文笔也明显优于同时代的其他地记作家。例如,《太平御览》卷四十九有甄烈《湘州记》和罗含《湘中记》两记对于石燕山的状写:
甄烈《湘州记》云:石形似燕,大小如一,山明云净,即翩翩飞翔。[286]
罗含《湘中记》云:石燕在零陵县,雷风,则群飞翩翩然。其土人未有见者,今合药或用。[287]
甄烈《湘州记》写“石形似燕”,只是比喻。而罗含《湘中记》故意隐去“似”字,把石燕山写得亦山亦燕,似幻似真,加上“雷风,则群飞翩翩然”一笔,化静为动,凸显景物的动感。又以“其土人未有见者”增加其神秘色彩,并回归现实,笔法高明。
总之,罗含《湘中记》的山水景物描写,已经为此后以山水描写见长的晋宋地记如袁山松《宜都记》、盛弘之《荆州记》等的创作,导夫先路。
(三)袁山松《宜都记》的文学色彩
袁山松,名崧,以字行[288]。按《晋书》卷八十三《袁瓌传附乔孙山松传》,“山松历显位,为吴郡太守。孙恩作乱,山松守沪渎,城陷被害”。复按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二《晋纪》,山松被害事在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又按《晋书·袁乔传》,山松祖袁乔尝为桓温司马,当与罗含为同时人。则袁山松当为东晋后期人,其所作《宜都记》必晚于罗含《湘中记》。
真正标志着中国山水散文创立的作品,应该是东晋袁山松《宜都记》。
这首先表现为山水审美观念的更新上。正如钱钟书所说:“诗文之及山水者,始则陈其形势产品,如京都之赋,或喻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尝玩物审美。继乃山川依傍田园,若茑萝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谢灵运《山居赋》所谓仲长愿言,应琚作书,铜陵卓氏,金谷石子,皆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即指此也。终则附庸而蔚成大国,殆在东晋乎?袁崧《宜都记》一节足供标识:其迭峨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词叙。林木萧萧,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游目赏心之致,前人抒写未曾。六法中山水一门于晋宋间应运突起,正亦斯情之流露,操术异而发兴同者。”[289]钱先生说“诗文之及山水者”“蔚成大国,殆在东晋乎”,即是指出山水散文形成于东晋。钱先生说“袁崧《宜都记》一节足供标识”则实际指出山水散文之于东晋形成,以袁山松《宜都记》为标志。
钱先生的看法是不错的。钱先生所引《宜都记》一节见于《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注》,其后尚有数句:“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290]这几句也极可注意,它是袁山松对自己山水审美自觉的直接表现。自觉,是自觉为“山水之美”的“千古”第一“知己”。这表示,袁山松肯定自己是山水自然审美自觉的第一人。袁的“知己观”则突破了此前以山水比德、证道的束缚,在山水审美自觉意识的深刻作用下,山水之美的描写第一次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以山水之美为知己,是山水散文的灵魂。仅此一点即可见,袁山松及其《宜都记》,厥功甚伟。
其次,袁山松《宜都记》,对山水自然作出了生动精彩的描写和记述。如:
对西陵南岸有山,其峰孤秀,人自山南上至顶,俯临大江如萦带,视舟船如凫雁。[291]
“俯临大江如萦带,视舟船如凫雁”,以江船之小来衬江山的辽阔,取喻之精妙,与明代张岱《湖心亭看雪》 “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的描写略相仿佛。
有时,袁大处落墨,取景壮大辽阔:
江北多连山,登之望江南诸山,数十百重,莫识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异势,自非烟褰雨霁,不辨见此远山。[292]
江山一色,绵亘不绝,百重千仞,大有气魄。
有时则精雕细刻,状物入微:
佷山县方山上有灵祠,祠中有特生一竹,擅美高危。其杪下垂,忽有尘秽,起风动竹,拂荡如扫。[293]
写轻风拂竹,竹动扫尘,如有灵性,竹的枝叶茂盛、风的轻逸已不待言而自出。画面层次分明,动静结合,把景物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最后,袁山松《宜都记》对其后的山水作品产生了许多有益的启发和影响。《宜都记》首先在写法上影响了其后的地记作品。如下面一则:
宜阳山有风井,穴大如瓮,夏出冬入。有樵人置笠穴口,风吸之,后于长杨溪口得笠,则知潜通也。[294]
比较同时代的《齐地记》,优劣自见:
《齐地记》曰:即墨城东西百八十里平昌城,高六丈,有台,有井与荆水通,失物於井,得之於荆水。[295]
《齐地记》只以“失物於井,得之於荆水”说明井与荆水通。这是一般性的记述,显得很平板。再看《宜都记》先写山之奇以作背景,再重点写风井潜通的特点,作者以“有樵人置笠穴口,风吸之,后于长杨溪口得笠”形容之,显得活灵活现,具有趣味横生的传奇色彩,给读者留下深刻而又明晰的印象。这样的写法,直接启发了刘宋盛弘之《荆州记》。例如,盛弘之《荆州记》的两条:
佷山县北陆行三十里有石穴,云昔有马从穴出,因复还入,潜行乃出汉中。汉中人失马亦入此穴,因名马穿穴。[296]
自游溪南行五十里有一泉。传云:南平江安县有牧羊者,见羊入此岸穴,当失之时,后乃闻出泉口,潜行可四百余里,因名为羊门。[297]
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是模仿《宜都记》来写的。
《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
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曦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298]
“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与前引“自非烟褰雨霁,不辨见此远山”笔法相近,直接影响了其后盛弘之《荆州记》及郦道元《水经注》“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日月”的写法。而“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对南朝梁吴均《与朱元思书》“泉水激石,泛泛作响”及《与顾章书》“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的写法似乎不无启发。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写游鱼一段,传神生动,历来备受传诵: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归根溯源,这也本之袁山松《宜都记》:
大江清浊分流,其水十丈见底,视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299]
“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空灵、生动、色彩绚丽,已开创出绝妙的“乘空”意境。袁山松最早写出的这“乘空”意境,唐代诗人也乐于吟咏。如杜审言《春日江津游望》:“飞棹乘空下,回流向日平。”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贯休《送新罗僧归本国》:“离岸乘空去,终年无所依。”莫不以“乘空”状江水之清澈。
总之,袁山松《宜都记》以全新的、审美的视角,主动与山水亲和,着意描写山水神态。从《宜都记》对山水自然的经典描写和从山水审美的自觉意识来看,袁山松的山水散文已经成为中国山水散文创立的标志。
(四)盛弘之《荆州记》的文学色彩
盛弘之《荆州记》是刘宋时期富于文采的地记作品的代表。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地理类云:“地志诸家,予独爱常璩《华阳国志》,次之则盛弘之《荆州记》。《荆州记》载鹿门事云:庞德公居汉之阴,司马德操宅州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记沮水幽胜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嵝倾岳,恒有落势。风泉传响于青林之下,岩猿流声于白云之上。游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给赏。若此二段,读之使人神游八极,信奇笔也。”[300]明王世贞也说:“正史之外,有以偏方为纪者,如刘知几所称地理,当以常璩《华阳国志》、盛弘之《荆州记》第一。”[301]
盛弘之《荆州记》能够赢得杨慎、王世贞诸人的青睐,正因为其以丰富多彩的文学性内容,特别是出色的山水刻画和景物描写见长。上述杨慎所引二条自不必说,盛弘之《荆州记》中生动形象的山水描写还不乏其例,如:
衡山有三峰极秀,一峰名芙蓉峰,最为竦桀,自非清霁素朝,不可望见,峰上有泉飞派,如一幅绢,分映青林,直注山下。[302]
《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引盛弘之《荆州记》,则作芙蓉峰“上有泉水飞流,如舒一幅白练”。以“白练”喻“流泉”,形象贴切,对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的写法似有启发。再如:
九疑山盘基数郡之界,连峰接岫,竞远争高,含霞卷雾,分天隔日。[303]
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回数百里,日月出没其中。湖南有青草山,因以为名。[304]
上节写九疑山,以四个排偶句式连贯而下,极写其高峻雄浑;下节写青草湖,状其阔大,则以“日月出没其中”为比喻。这是继承了曹操《观沧海》诗“日月之行,如出其中”及《湘中记》“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的写法。
就是写小山小水,盛弘之《荆州记》也往往写得清新雅致:
修竹亭西一峰迥然,西映落月,远而望之,全如画扇。[305]
都梁县有小山,山上水极浅。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谷。俗谓兰为都梁,即以号县云。[306]
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绿条散风,清阴交陌。[307]
有的山水景观是因其物色之独特以命名的,盛弘之的描写就突出强化其特点:
宜都西陵峡中,有黄牛山,江湍纡回,途经信宿,犹望见之,行者语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日三暮,黄牛如故。[308]
在这里,盛弘之以形象化的手法逼真地描述了“江湍纡回”的情状,富有传神意味,引来唐代著名诗人纷纷为之提笔作诗,如李白《上三峡》:“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杜甫《送韩十四江东觐省》:“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
盛弘之《荆州记》中的山水描写,较袁山松《宜都记》的描写,更为细致生动。例如:
袁山松《宜都记》曰:虎牙山有石壁,其色黄,间有白文,亦有牙齿形。[309]
盛弘之《荆州记》曰:郡西溯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门。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对,楚之西塞也。虎牙,石壁红色,间有白文,如牙齿状。荆门,上合下开,开达山南,有门形,故因以为名。[310]
《荆州记》是把荆门山和虎牙山结合在一起来写的,不但用贴切的比喻写出了两山各自的特点,还点明两山地理位置的重要:“楚之西塞也。”从可感性方面看,《荆州记》略胜于《宜都记》。《荆州记》自觉地借鉴吸收了《宜都记》的描写成果,而又润色之,后出转精。
众所周知,《水经注》中最为精彩的山水描写,也是奠定《水经注》文学价值最为重要的内容,当为卷三十四《江水注》中的《三峡》一节。而这段文字本从盛弘之《荆州记》中脱化而来:
盛弘之《荆州记》曰:旧云自二峡取蜀数千里中,恒是一山,此盖好大之言也。惟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云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为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渌潭,回清到影,绝巘多生柽,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雅趣。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311]
作者先写山势,在否定传言“恒是一山”时,就已引人注意峡谷之奇了。而后极其笔力铺写山之“连”与“高”的特色。写山“连”:“略无阙处”;状山“高”:“隐天蔽日。”作者运用艺术夸张的手法,把峡谷幽深阴晦的特点进行表现。正笔之后,紧接以侧笔烘托:“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引发读者对其予以想象,以得到一个更具体更形象的印象。山高则流必急。写水重点描绘其“疾”。而四季中尤以夏水最为迅猛,因此作者打破时间顺序,先写“夏水襄陵”,体现了布局的匠心。“沿溯阻绝”,既是对水流之急水势之险的补写,也是下文“王命急宣”的伏笔。既然是“急宣”,当然要选择最迅速的交通方式。而这最迅速的交通方式是什么?自然是取道三峡,乘舟而下。作者写道:“有时云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为疾也。”通过时间短、距离长的对比描写,明写舟行之神速,暗点江流之迅猛,用的仍是侧笔烘托之法,而且,与“沿溯阻绝”的滞塞情形相对照,文意飞动,波澜顿生。陆游《入蜀记》写三峡“初冬草木皆青苍不凋”,可见三峡冬暖,有似于春。因此,作者把春冬合起来写。写春冬,突出的是“趣”。作者先用一个“则”字一转,引出了与夏季山森水急不同的另一番意境:水退潭清,山峰峻峭,再点缀以悬泉瀑布,配合以茂盛的草木,宛如工笔山水画图。最后写秋,不着“秋”字而以“霜”字巧妙暗示,描写重点在“肃”。作者调动视觉、触觉、听觉多种感官配合描写,“肃”因“寒”生,“凄”由“肃”起,在袅袅渔歌中不绝如缕。
此段文字历来备受称许,也为许多后代诗文作家常所借鉴。杨慎《丹铅馀录》:“《荆州记》,盛弘之撰,其记三峡水急云: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余里,虽飞云迅鸟,不能过也。李太白诗云: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杜子美云:朝发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语也。”[312]当然,盛弘之写舟行之速,也是受了东晋袁山松《宜都记》“自蜀至此,五千余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313]这一写法的启发。但盛弘之《荆州记》比袁山松《宜都记》写得更加形象、生动。
这段文字中描写的“听猿”景状,也成为唐代诗人乐于吟咏的意象,构成了唐诗的某种独特意境。如宋之问《发端州初入西江》:“破颜看鹊喜,拭泪听猿啼”,李白《姑孰十咏·牛渚矶》:“更听猿夜啼,忧心醉江上”,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杜甫《秋兴》:“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贾岛《送惠雅法师归玉泉》:“饮泉看月别,下峡听猿愁”,杜荀鹤《秋夜闻砧》:“不及巴山听猿夜,三声中有不愁声”,不可胜举。
由此可见,盛弘之《荆州记》的山水描写,笔法更加生动细致,其中有许多已是独立成形的山水短章。从山水审美情趣的确立,选材布景的合理安排,描写篇幅的加长,山水刻画技巧的提高以及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诸方面来看,盛弘之《荆州记》标志着中国山水散文已经成熟。
唐杜佑《通典·州郡部》云:“凡言地理者多矣,在区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纤介毕书,树石无漏,动盈百轴,岂所谓撮机要者乎!如诞而不经,偏记杂说,何暇编举(自注云: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谬,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314]杜氏从史家著述应该严肃认真的角度对诸地记痛下贬语。实际上诸地记“纤介毕书,树石无漏”,正是其文学性内容增强的反映。诸地记正是企图通过富有文采的记述和描写,来调动阅读者的兴趣,激发他们对作品中所写胜境的向往,对地方自然、人文和历史的感受和思索。
中国山水散文经过汉代辛氏《三秦记》所代表的萌芽阶段,东晋罗含《湘中记》和袁山松《宜都记》所代表的创立阶段,刘宋盛弘之《荆州记》所代表的成熟阶段,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已走向高度发展阶段。《水经注》正是因为吸收了大量南朝地记的优秀成果,博采众家山水描写之所长,才成为中国山水散文早期的典范之作。
[1](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2](唐)徐坚等撰:《初学记》卷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页。以下版本同。
[3](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六十六湖,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3页。以下版本同。
[4]《太平御览》卷九六二竹上,第4271页。
[5](唐)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卷八山部下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以下版本同。
[6]《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墨,第2723页。
[7]《艺文类聚》卷七山部上,第122页。
[8]《太平御览》卷八五九粥,第3816页。
[9]《艺文类聚》,第230页。
[10]《太平御览》卷三三八角,第1550页。
[11]《太平御览》卷五七六磬,第2599页。
[12]《太平御览》卷五十四穴,第263页。
[13]《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地部三十,第311页。
[14]《初学记》卷五华山,第99页。
[15]《初学记》卷五总载山,第92页。
[16]《初学记》卷五,第97—98页。
[17]《初学记》卷六江,第125页。
[18]《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地部六,第195页。
[19]谢凝高:《山水审美:人与自然的交响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20]《水经注疏》,第2844—2845页。
[21][加拿大] 卡尔松:《环境美学:自然、艺术与建筑的鉴赏》,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22]宗白华:《论 〈世说新语〉 和晋人的美》,《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23]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
[24]《水经注疏》,第2698页。
[25]《水经注疏》,第2327页。
[26](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襄阳,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14页。
[27]《水经注疏》,第3145页。
[28]《水经注疏》,第2836页。
[29]《太平御览》,第206页。
[30](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注引,(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89页。
[31]《太平御览》卷五十四穴,第263页。
[32]《艺文类聚》卷六冈,第105页。
[33]《水经注疏》,第3121页。
[34]《水经注疏》,第2847页。
[35](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34页。
[36]刘洁:《美境玄心:魏晋南北朝山水审美之空间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37]《初学记》,第295页。
[38]《太平御览》卷四十七地部十二,第229页。
[39](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第1531页。
[40]《太平御览》卷四十一九疑山,第198页。
[41](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第1579页。
[42](明)杨慎:《升庵集》卷五十二,《四库全书》第12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8—449页。
[43](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第123页。
[44]《太平御览》卷六十九洲,第327页。
[45](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六“沅陵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7页。
[46]《太平御览》卷五七二歌,第2586页。
[47]《初学记》卷八山南道,第181页。
[48]《太平御览》卷四十三桐柏山,第206页。
[49]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50]《太平御览》卷五十地部十五,第243页。
[51](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六,祝洙增订,施金和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8页。
[52]《太平御览》卷六十九洲,第327页。
[53](南朝梁)萧统:《文选》,曹子建《王仲宣诔》注,(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5页。
[54](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当阳县,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48页。
[55]《方舆胜览》卷二二南安军,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04页。
[56]《太平御览》卷五七二歌,第2586页。
[57]《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州郡部鄂州,第829页。
[58]《艺文类聚》,第1652页。
[59]《艺文类聚》,第295页。
[60](南朝梁)刘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史传》第十六,黄叔林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7页。
[61]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辑:《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105—2130页。以下版本同。
[62]《二十五史补编》,第4943—5037页。
[63]《二十五史补编》,第3797—3849页。
[64]《二十五史补编》,第3703—3759页。
[65]《二十五史补编》,第3895—3965页。
[66]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 及其 〈杂传类〉 的分析》,《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0页。
[67](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校注》,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85页。以下版本同。
[68](晋)袁宏撰:《后汉纪》孝明皇帝上卷永平元年,周天游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
[69]王卫婷:《魏晋南北朝州郡地记与地域意识略述》,《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70]《华阳国志校注》,第881—882页。
[71](唐)刘知几撰:《史通通释》,(清)浦起龙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6页。
[72]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73]《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第1243页。
[74]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页。
[75]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76](清)章学诚撰:《文史通义新编校注》州县请立志科议,仓修良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36页。
[77](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刘公纯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50页。
[78]《水经注》汝水注引,《水经注疏》,第1785—1786页。
[79]《太平御览》卷四二六清廉下引,第1963页。
[80]《太平御览》卷二十六冬上引,第125页。
[81]《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引,《水经注疏》,第3130页。
[82]《太平御览》卷八九七兽部·马引,第3983页。
[83]《太平御览》卷四二一人事部·义引,第1944页。
[84]《艺文类聚》卷四十九太常引,第879页。
[85]《艺文类聚》卷五十令长引,第910页。
[86]《太平御览》卷五五六葬送四引,第2515页。
[87]《太平御览》卷九六八果部·杏引,第4292页。
[88]《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十杖引,第2907页。
[89]《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七人事部·舌引,第1694页。
[90]《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五主簿引,第1240页。
[91]《太平御览》卷四二六清廉引,第1963页。
[92](宋)李昉:《太平广记》第二三四卷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97页。
[93]《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8页。
[94]《太平御览》卷四八八泣引,第2234页。
[95]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0—581页。以下版本同。
[96]《太平御览》卷五一六兄弟引,第2348页。
[97]《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六友悌引,第1920页。
[98]《三国志·刘二牧传》裴松之注引,《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01页。
[99]《水经注》卷三十六延江水引,《水经注疏》,第2970—2971页。
[100]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
[101]《太平御览》卷七七一舟部引,第3419页。
[102]《三国志·吴书·妃殡传》裴松之注引,《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3页。
[103]《太平御览》卷四三二聪敏引,第1992页。
[104]《太平御览》卷四四四知人引,第2044页。
[105]《太平御览》卷四百三道德引,第1864页。
[106](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袁安传》注引,(唐)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18页。
[107]《太平御览》卷一五八开封府引,第767页。
[108]《后汉书·庞公传》注引,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77页。
[109]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6页。
[110]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11]《世说新语》方正篇注引,《世说新语笺疏》,第280页。
[112]《初学记》卷二十二武部剑引,第528页。
[113]《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世说新语笺疏》,第1页。
[114]《太平御览》卷一六八房州引,第817页。
[115]《初学记》卷六地部中江引,第125页。
[116]《三国志·张纮传》裴松之注引,《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页。
[117]《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引,第1864页。
[118]《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五幼智引,第1781页。
[119](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四库全书本第889册)卷一百一十八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7页。以下版本同。
[120]《三国志·刘表传》裴松之注引,《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121]《太平御览》卷四九二贪引,第2251页。
[122]《太平御览》卷四二六清廉引,第1963页。
[123]《太平御览》卷三六八颐颔引,第1698页。
[124]《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九容止引,第1801页。
[125]《太平御览》卷二六九县尉引,第1260页。
[126]《三国志·蜀志·刘巴传》裴松之注引,《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05页。
[127]《三国志·蜀志·刘巴传》裴松之注引,《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06页。
[128]《太平御览》卷四百十父子交引,第1892页。
[129]《太平御览》卷九七三椹引,第4315页。
[130]《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六人事部清廉引,第1963页。
[131]《艺文类聚》卷五八书引,第1040页。
[132]《太平御览》卷九百牛引,第3993页。
[133]《艺文类聚》卷五岁时下腊引,第93页。
[134]《太平御览》卷五一一引,第2325页。
[135]《太平御览》卷九二一鸠引,第4088页。
[136]《太平御览》卷八六八火引,第3849页。
[137]《艺文类聚》卷八三金引,第1423—1424页。
[138]《艺文类聚》卷九十七蝇引,第1681页。
[139]《太平御览》卷四二一引,第1943页。
[140]《太平御览》卷六二汉沔引,第298页。
[141]《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六兵部·匕首引,第1594页。
[142]《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引,《世说新语笺疏》,第4页。
[143]《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功曹参军引,第1237页。
[144]《太平御览》卷二四八职官部王文学引,第1170页。
[145]《艺文类聚》卷九水部下池引,第171页。
[146]程千帆:《闲堂文薮》之第二辑《汉魏六朝文学散论》之二《史传文学与传记之发展》,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62页。
[147]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第一章《序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148](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451页。
[149](清)顾炎武撰:《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2—2263页。
[150]陶弘景语,见(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97页。
[151](梁)刘勰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页。
[152][日] 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韩基国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153]柳治微:《中国文化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页。
[154]见《礼记·祭法》,《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第1588页。
[155]《艺文类聚》卷四十三乐部三引,第772页。
[156]《艺文类聚》卷六峡三引,第106—107页。
[157]《初学记》卷八江南道引,第188页。
[158]《水经注》卷十五洛水引,《水经注疏》,第1315—1316页。
[159]《太平御览》卷七十渊引,第330页。
[160]《太平御览》卷七十渊引,第330页。
[161]《太平御览》卷十一祈雨引,第56页。
[162]《太平御览》卷十一祈雨引,第56页。
[163]《太平御览》卷十一祈雨引,第56页。
[164]《初学记》卷二雨引,第24页。
[165]《太平御览》卷五十四岩引,第262页。
[166]《太平御览》卷四十七坛宴山引,第228页。
[167]《太平御览》卷四十八引,第235页。
[168]《太平广记》卷一一八报应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24页。
[169]《初学记》卷七昆明池引《关中记》,第148页。
[170]《太平御览》卷四八二仇引,第2208页。
[171](唐)虞世南撰:《北堂书钞》卷八九,第46页。
[172]《太平御览》卷九百十六鹤引,第4060页。
[173]《太平御览》卷四十七乌带山引,第228页。
[17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四库全书本卷一六四端溪县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9—520页。
[175]《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刀上引,第1589—1590页。
[176]《初学记》卷八江南道引,第187页。
[177][法]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6页。
[178]《太平御览》卷九四二蟹引,第4185页。
[179]《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爪引,第1707页。
[180]《太平广记》卷四六八水族五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855页。
[181]参见(汉)刘安《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5页。
[182]《太平御览》卷九五九棘引,第4257页。
[183]《太平御览》卷六星引,第31页。
[184]《太平御览》一七一衡州引,第834页。
[185]《太平御览》卷三九八吉梦引,第1839页。
[186]《初学记》卷二霁晴引,第40页。
[187]《太平御览》卷三六四头引,第1677页。
[188]《太平御览》卷三六六耳引,第1684页。
[189]《晋书》,第2467页。
[190]参见(晋)葛洪《抱朴子·微旨》,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5页。
[191]《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注引,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50页。
[192]《艺文类聚》卷九六蛟引,第1664页。
[193]《太平御览》卷九五九黄蘖引,第4257页。
[194]《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古度引,第4262页。
[195]《太平御览》卷八八六精引,第3937页。
[196]《太平御览》卷四十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6页。
[197]《太平广记》卷二九四神四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342页。
[198]《太平御览》卷七七一牂柯引,第2420页。
[199]《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二银引,第3609页。
[200]《太平御览》卷八一一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605页。
[201]《太平御览》卷四九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2页。
[202]《太平御览》卷九六三笋引,第4276页。
[203]《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冢墓引,第2529页。
[204]《艺文类聚》卷七十九神引,第1347页。
[205]《太平御览》卷二九元日引,第136页。
[206]《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九十一神一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315页。
[20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208]《太平御览》卷八八六精引,第3937页。
[209]《太平御览》卷三三八鼙引,第1552页。
[210]《太平御览》卷六六湖引,第315页。
[2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12]鲁迅:《何典》题记,《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213]《太平御览》卷二六九县尉引,第1260页。
[214]《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五血引,第1733页。
[215]钱谷融:《文学心理学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216]《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二歌引,第2586页。
[217]《太平御览》卷九九五藤引,第4405页。
[218]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219]《太平御览》卷五五六葬送引,第2516页。
[220]刘湘兰:《中古叙事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221]《太平御览》卷九六五枣引,第4282页。
[222]《太平御览》卷七九一朱提引,第3509页。
[223]《太平御览》卷七九六獠引,第3534页。
[224]《太平广记》卷四二五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460页。
[225](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226]《太平御览》卷九一八鸡引,第4073页。
[227](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一,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89页。
[228]《太平御览》卷七九一邛引,第3506页。
[229][德]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王太庆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38—439页。
[230]《太平御览》卷九四一螺引,第4181页。
[231]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7—358页。
[232]《水经注疏》,第3059页。
[233]《水经注疏》,第2848页。
[234](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235]徐成志:《锦绣河山竟风流——中华山水文化解读》,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185页。
[236]《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第1588页。
[237]见《论语·庸也》。
[238]见王弼《老子注》第四十一章。
[239]《世说新语笺疏》,第616页。
[240](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30页。
[241]《水经注疏》,第2845页。
[242](汉)董仲舒:《董子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页。
[243]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3页。
[244](清)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311页。以下版本同。
[245]《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311页。
[246]《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335页。
[247]《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341页。
[248]《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784页。
[249]参见笔者博士学位论文《水经注文献学文学研究》。
[250]《水经注疏》,第3063页。
[251]王立群:《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
[252]《太平御览》卷六十六引,第315页。
[253]《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世说新语笺疏》,第145页。
[254]《太平御览》卷五五六卷葬送引,第2514页。
[255]《太平寰宇记》四库全书本卷九十三於潜县引,第41页。
[256]《太平御览》卷四十六引,第224页。
[257]《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逸民引,第2323页。
[258]《太平御览》卷五十契吴山引,第243页。
[259]《太平御览》卷七十四沙引,第349页。
[260]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261](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0页。以下版本同。
[262](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59页。
[263](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43页。
[264](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3页。以下版本同。
[265](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78页。
[266](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5页。
[267](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页。
[268](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3页。
[269](唐)刘知几撰:《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270]引自张英聘《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
[271]《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地部四引,第186页。
[272]《艺文类聚》卷七,《初学记》卷五地理上及《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地部四引罗含《湘中记》。
[273]《艺文类聚》卷七,《初学记》卷五地理上及《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地部四引辛氏《三秦记》。
[274]《太平御览》卷五十地部十五引,第245页。
[275]《水经·河水注》《太平御览》卷七十四、《资治通鉴》晋义熙元年注并引段国《沙州记》。
[276]《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张守节《正义》引《三秦记》。《艺文类聚》卷九十六、《初学记》《文选》卷三十、《通典》卷一百七十九州郡九、《后汉书》注、《括地志》《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太平寰宇记》《草堂诗笺》都曾引,略同。
[277]《太平御览》卷四十、《太平寰宇记》《长安志》引辛氏《三秦记》。
[278]《晋书》卷九十二《罗含传》:“刺史庾亮以为部江夏从事。……后桓温临州,又补征西参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03页。
[279]《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咸康六年薨,时年五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23页。
[280]《艺文类聚》卷七引罗含《湘中记》。《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地部六》引《湘中记》同。
[281]《初学记》卷五地理上引罗含《湘中记》,第97页。
[282]《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引罗含《湘中记》,《艺文类聚》卷八引略同,《太平御览》卷七十四引稍略,又《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南兖州记》曰:瓜步山东五里,江有赤岸山,南临江中。罗君章云,赤岸若朝霞,即此是也。”
[283]《初学记》卷五地理上引罗含《湘中记》,第98页。
[284]《水经注》卷三十八引罗含《湘中记》,《水经注疏》,第3121页。
[285]见《升庵诗话·子传记语似诗者》,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5—646页。
[286]《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第241页。
[287]《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第241页。
[288]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宜都山川记叙录》:“考《晋书》目录于袁瓌下列瓌子乔,孙崧;而于瓌本传则云乔子方平,方平子山松,明崧与山松只一人,山松则离而为字也。”
[289]《管锥编》全汉文卷八九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7页。
[290]《水经注疏》,第2845页。
[291]《初学记》卷六地部中·江引袁山松《宜都记》,《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注、《太平御览》卷六十江引同,《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并尝引之。
[292]《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引袁山松《宜都记》,《水经注疏》,第2848页。
[293]《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二《竹》引袁山松《宜都记》,《艺文类聚》卷七山部引稍异。
[294]《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袁山松《宜都记》,第239页。
[295]《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城上,第929页。
[296]《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八《穴》引盛弘之《荆州记》。
[297]《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八《穴》引盛弘之《荆州记》。
[298]《水经注疏》,第2844—2845页。
[299]《太平御览》卷六十江引袁山松《宜都记》,第290页。
[300]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7页。
[301]见(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302]《艺文类聚》卷七山部上引,第233页。
[303]《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引,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一册,夏剑钦、黄巽斋校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
[304]《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盛弘之《荆州记》,第140页。
[305]《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江陵县引盛弘之《荆州记》。
[306]《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三引盛弘之《荆州记》,第4352页。
[307]见《艺文类聚》卷八十九《木部下》引盛弘之《荆州记》,《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七引同,《水经注》卷三十四: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
[308]《艺文类聚》卷七山部上引,第122页。
[309]《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夷陵县引袁山松《宜都记》。
[310]《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0页。
[311]《太平御览》卷五十三引盛弘之《荆州记》,第259页。
[312](明)杨慎:《丹铅馀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2年版。
[313]《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水经注疏》,第2843页。
[314]参见(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