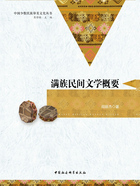
绪论
中国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间文学,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学和本民族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地理位置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满族民间文学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满族民间文学是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族民间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化特质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满族民间文学是满族民众集体创作、世代以口头传承为主的一种语言艺术。满族民间文学以口头语言为主要载体,大胆地抒发民众的情感,塑造具有满族民族特点的艺术形象,通过叙述故事展示满族独特的话语构成。满族民间文学往往是世代传承的结果,在传承过程中,被不同的作者不断地加以改编,因而,满族民间文学是满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某一个天才作家的创作。
“艺术科学的研究应该扩展到一切的民族中间去,对于从前最被忽视的民族,尤其应该加以特别注意。”[1]
满族民间文学总体特征如下。
第一,满族民间文学和一般的专业文人创作是有区别的,满族民间文学和满族民众的联系更密切,甚至有些满族民间文学本身就是满族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很多满族民间文学本身具有二重性,它既属于生活本身,又属于文学艺术。有些作品很难区分是属于生活的还是属于艺术的。如满族的萨满神歌、满族的劳动歌谣,既是满族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又是文学作品,满族民间文学和生活呈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亲和状态。
第二,满族民间文学往往是口头传承的,即口碑文学。金史记载:“女直(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太宗初即位,复进士举,而韩昉辈皆在朝廷,文学之士稍拔擢用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十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金史》卷六十六)
第三,满族民间文学不是突出某个天才作家,而是某类民间文学作品的丰富多彩。作品的丰富性在于类型的丰富性。满族民间文学为民众所创作,在民众中流传,被民众所接受。在满族民间文学中,很难找到作品的原创者,我们找到的往往只是传承人。满族民间文学作品往往是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是集体传承、创作的结果。
第四,满族民间文学呈波浪式发展的传承态势。(1)满族民间文学的传承主要在口耳之间,少有文字记载,因而在传承过程中,总会有不一致的地方。(2)满族文学是民间集体传承,因此,每个传承人对于作品的传承会多少有些出入。但总体来看,满族民间文学不论怎样传承,万变不离其宗,作品总体框架保持不变,满族民族特色不变。
满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每一次传承都有艺术再创造的成分,传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因素对作品进行加工润色,打上个人的主观烙印。
第五,满族民间文学表现了满族人特有的民族心理。满族的民族心理决定了满族的语言、思想、信仰、习俗等和其他民族是不同的,这导致了满族民间说唱艺术的创作与汉族不同。
首先,满族文学作品中满族作家表现出了满族特有的民族自主意识。满族文学作品中表现了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自豪感,而汉族的诗词往往表现故国之思、兴亡之感,明末清初的汉族作家有这种心态的很多。清朝满族诗人吴兰雪写道:“边墙踏破中原定,帝铭彤弓拜家庆。箭传三尺六寸长,百石能开猿臂强。”[2]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满族入主中原的自豪感。“清以异族入主中原,汉人多有家国陆沉之痛。”[3]明末清初,明代遗民人数众多,有关文献资料较为丰富,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明末清初三大遗民思想家,八大山人等遗民画家以画喻时言志,都表现出了兴亡之感。钱谦益的《投笔集》系晚年之作,多抒发反对清朝、恢复故国的心愿。乾隆时,他的诗文集遭到禁毁。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钱谦益“文化遗民”的面目。
其次,满族文学作品在继承汉族文学作品时,以满族的民族心理为创作的依据,继而修改汉族文学作品的主题,把满汉冲突改成爱情冲突。从《桃花扇》里也可以看出满族和汉族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的民族心理差异。汉族作家孔尚任的《桃花扇》用所谓“春秋笔法”,描写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悲剧。当时各省起兵抗清的前后三藩早已平定,孔尚任是借离合之情,写南明兴亡之感。孔尚任在《桃花扇》的结尾写道:“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4]这种感受不是满族作家所有的。同样是写《桃花扇》,满族作家和汉族作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满族作家只写了爱情的悲剧,而把兴亡感抹掉了。八旗子弟书中写的《守楼》,选自《桃花扇》中的一段,把李香君血染桃花扇的起因改成是由于有人逼婚所致,李香君的死完全没有了兴亡之感,完全抹杀了其中的政治因素。“只因为当朝宰相贵阳的亲戚,田百源他后房思聘一美多娇。久闻令爱多姿色,特恳我在旧院红楼访一遭……他相府的吉时错不得分毫。逼的个香君无可奈,芳心一狠转纤腰。花容碰在楼窗上,晕倒在尘埃血点儿飘……昏沉多会才苏醒,见那素扇洇湿都是血点儿抛。”[5]同样是《桃花扇》,汉族和满族处理的方式完全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心理差异造成的。
对于《孟姜女》故事,汉族和满族创作的民族心理也是不同的。长城是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秦始皇修长城,是因为害怕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据史料记载,一个叫卢生的方士,受始皇之命出海,回来后,给始皇带回了句话,说:“亡秦者,胡也。”另外,只有在北方修筑长城,才能抽调主要兵力,用于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和保卫战争,才能完成统一大业。因此,秦始皇动用了秦国全国的国力,让多少老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这样才产生了汉族的民间故事《孟姜女》。而在满族创作的关于孟姜女的《满汉合璧寻夫曲》中,省略了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起因,“吕不韦妻怀贪种贪秦业,贪根子生出贪种作贪贼。孟子说固国不以山溪为险,秦始皇偏筑长城白骨成堆。害尽苍生天地惨,毒流四海鬼神悲”[6]。可见,在满族文学作品中,潜在的民族创作心理改变了修长城的起因。满族的文学创作趋向于满汉融合。
第六,满族民间文学与汉族文化呈逐渐渗透的状态。
满族民间文学总体上有个特点,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文学与汉族文化日渐渗透,越到后期,满族民间文学渔猎文化的因素越少,农业文化的因素越多。
[1]朱狄:《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27页。
[2](清)昭梿撰:《啸亭杂录》,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299页。
[3]张家生:《八旗十论》,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年版,第5页。
[4](清)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261—262页。
[5]张寿崇主编:《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守楼》,民族出版社 2000年版,第370页。
[6]张寿崇主编:《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守楼》,民族出版社 2000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