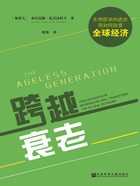
科学革命的结构
科学发展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很难追赶上它发展的节奏。更糟糕的是,改变旧有的观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些长时间存在或贯穿于一个人一生中的观念是如此难以抹去,而不论背后的科学道理是多么的显而易见。实际上,一项全新的科学发现从出现并开始冲击旧有的科学观念到科学家及民众广为接受这种新的科学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时间上的滞后现象。
从理论上讲,这种滞后障碍压根不应该存在才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正确与否不取决于我做实验的数量,一次不成功的实验就能证明我的失败。”爱因斯坦这一简单却不失优雅的说法抓住了科学的精髓。一次站得住脚的实验(经过了正确记录和独立重复检验)就应该能够改变旧有的科学观念。但在实际当中,由于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来自科学界的或人为的偏见,这种本该正常的情况却鲜有发生。
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她的成名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科学的前进并不仅仅是以客观标准或新知识的线性叠加为依据的。与此相反,所谓的科学“事实”恰恰是被当今科学界所公认的共识所决定的。当某种新发现出现的时候,科学家们是并不愿意接受那些同主流学界公认理论相悖的任何观点的。库恩的观点是:科学的真正进步必须首先是新理论被足够多的科学家们所接受,直到新理论达到了一个被广为接受的临界点。只有在这个临界点,新的理论才能替代旧有的理论。库恩还创造出了一个术语,专门用来描述这个临界点(即从一种主要的共识结构转变为另一种共识结构的临界点),即著名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s)。
不幸的是,不管对医学研究者而言还是对饱受老年病困扰的患者而言,这一科学共识的转换通常会发生在新发现被证实后的许多年。医药科学的历史充满着由于教条的信念而使医学发展减缓的例子。医学专家花了半个世纪才确认了“洗手对人有好处”这个事实,但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早在1848年时便知道了。1918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由于其在量子物理学的新发现被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当时曾意味深长地说道:“一项新的科学事实并不是通过规劝对手信服而取得成功的……,而是因为对手们最后终于都死掉了。”再后来,普朗克更为简单地讽刺道:“科学的每一次进展都要奠基一座坟墓。”
虽然今天医学界的共识为“衰老是不能够减缓和避免的”,但范式转换的发生却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今天的医学进展已经能够使老年人活得更为长久(不一定在健康的情况下)。同几十年前老年人遇到绝症必死无疑相比,今天的老年人虽然能活得更久一些,但往往是刚从一种病魔手中逃过一劫,就又要遭遇另一种治疗起来同样价格不菲的顽疾。老年人医疗保险的花费也因此而水涨船高,让人瞠目不已。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为何却仅有少数胸怀梦想的科学家愿意站出来大声疾呼,表示要对衰老进行宣战并开展为恢复人体功能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呢?为何这一让人兴奋的新范式很难抓住全世界科学家的想象力呢?也许就如同库恩解释的那样:改变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种变化现在正在加速发生,而且这一速度已经很快了,以至于不论世界的领导人或是很多的科学家想要继续跟上医学进步的变化速度都感到勉为其难。
同前人费力而又缓慢的医学研究相比,今天的研究模式大为不同,而这要归功于个人电脑的广泛使用。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戈登·摩尔首先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该定律预测计算机的能力每隔两年就会翻一番。在计算机能力提升的预测方面,摩尔定律已被证明有着出奇的准确性,而计算机能力的提升也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新医学发现的进步。正当怀疑的论调认为摩尔定律仅仅只能再持续几年的时间时(因为芯片的元件不能无视物理法则而无限地缩小下去),工程师们已经开始尝试运用下一代的电脑来打破极限了。这些最新的前沿技术包括光子计算机、DNA计算机、电子自旋计算机及能模拟大脑神经元运算的化学计算机。当硅片达到某种极限而无法再微型化的时候,这些新型计算机技术的某一种便有可能在未来出现并取代今天的电脑。计算能力每两年就能持续翻一番带来的启示几乎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这使一些曾经耗时好几年并且耗资巨大的项目变得非常简单,一些中学生就能在自己的科研计划中完成。
想象一下以下这个例子为我们带来的启示吧!曾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计算科研项目就是1989年由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研究所(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研究所本身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组织成立)负责的“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这一项目当时预期耗时数十年,其结果将会最终确定DNA当中的30亿个碱基对的排序工作及同时识别人类基因中的2.3万个基因。这一计划的最终完成是在10年之前,这项对人类基因首次测序的工作共耗费了13年,并花掉了30亿美元。这项研究耗费巨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当时需要的计算能力太大。
时至今日,多亏了迅速增长的计算机能力,基因测序能在少于1万美元的成本下完成,并且这一花费还在持续下降。在一家名为“23和我”的私人基因测序公司(“23和我”英文为“23 and Me”,这家公司名字当中的数字23源自人类基因中的23对染色体。“23和我”基因公司是由安妮·沃茨克奇女士成立的。安妮也是谷歌公司的共同创办人之一——谢尔盖·布林的夫人。),仅仅需要99美元,您就能对自己数以万计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得到一个完整的检测,且这一过程非常简单。消费者仅仅需要把自己的一口唾液样本邮寄给“23和我”基因公司就可以了,之后他们会通过网络给出检测结果。我个人在2009年参与了这个检测,现在我还能定期收到他们提供给我的关于我基因的一些最新信息。现在,全世界有超过12.5万人正在使用“23和我”或其他类似公司的相关业务。这些人不仅通过基因测序的结果来寻根问祖,而且还能预测自己未来有哪些易患疾病的倾向、确定自己是哪些致病基因的携带者。随着数据库的扩大,这一过程最终能够确定疾病诊断及治疗的新方法,制造高级诊断性药物,建立一个同某些高危病症资料联网的相关基因数据库。
医学科技最近进展神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其他一些非医学专业对医学科技进步的持续性贡献。就拿数学来说吧,您也许没听说过“傅里叶变换”。这是种用来简化信息的数学方法,但这种方法也被用来压缩大量的信息,从电脑里的JPEG格式的图像文件到常用的mp3格式的音乐文件都采用了傅里叶变换的压缩方法。在医学研究领域中,傅里叶变换被用于从核磁共振分析结果中提取数据并形成直观的图像,以便用来帮助医生进一步诊断疾病。数学算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医疗领域,这些领域包含从数据分析到诊断的一系列过程。数学还被广泛运用于计算机建模当中,如运用流体动力学方程来理解血液在静脉和动脉中是如何流动的。一些诸如核磁共振影像及超声波影像的医学图像也是运用数学方程来制作的。
另一些医学前沿研究所用的科技就太先进了,它们看起来就像是电影《星际迷航》里所描述的那样。当纳米科技融合了机械工程、信息技术及数学领域的科技成果,就可能从单一的原子上制造微型机器人。这种机器人也许只有几纳米的宽度,这比人类头发的直径还要小许多。多年之后,纳米技术会扩展到机器和电脑范围之外的领域进行实践运用。纳米技术在这些新领域中的应用如此激动人心。在未来,嵌入衣服的纳米管能够使衣服跟随天气的变化而改变颜色,或者直接根据使用需要让衣服在透气纤维模式和防水模式中自行切换。军事科学家预言纳米管纤维能在撞击过程中变硬,制造一层爆炸无法穿透的障碍,并且能与此同时保持一定的舒适性以减缓疲劳。纳米科技对医学而言也有着极其光明的前景。
2006年,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运用一种名为“近红外激光”(near-infrared lasers,一种比可见光光波更长一些,却对人体组织无害的激光)的激光进行了一次试验。这种“近红外激光”能在两分钟内将人造的碳纳米管加热至华氏158度(约摄氏70度)。这些纳米管随后被注入一颗已经癌变的肿瘤之中,并给一段时间,使它们和癌细胞充分相互融合。随后,这颗肿瘤被放置到这种“近红外激光”下进行试验。这场实验结果是:癌细胞都被杀死了,而与之相邻的其他正常细胞则毫发无损。
由于一个细胞能装下成千上万的纳米管,将它们暴露于近红外激光能为科学家在细胞尺度上有效地瞄准癌细胞。但这一方法也有其困难之处,只将纳米管送到癌细胞内部而不是周边的正常细胞内部是有一定难度的。但这一难题也被攻克了,科学家使用的方法是将纳米管用叶酸(一种维生素B)进行包裹。同一般的正常细胞不同,癌细胞身上有着丰富的叶酸感受器。当癌细胞遇到被叶酸包裹的纳米管时,癌细胞就像是磁铁遇到铁那样,会把这些叶酸碳纳米管全部吸进去。
目前这一方法尚处于试验阶段,但日后一旦成功,近红外激光就会成为科学家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治愈癌症的利器。这一方法使用的工具也并非十分昂贵,低功率的近红外激光已经在非接触式婴儿温度计当中被广泛地使用了。如果这种向癌细胞定向投送纳米管的技术能够通过临床试验,这一方法就可以改变医疗行业。今天,癌症是排在心脏病之后的老年人的第二号杀手,但是近红外激光及其他一些生物医学的进展已允许人们使用很少的成本治愈癌症,并且这种治疗方式是非侵入式的和无副作用的。
在另一些情形下,很多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在它们能被广泛运用前就已经过时了,这其中的代表之一就是质子治疗仪。质子射线治疗技术是一种极其先进的、利用计算机控制的大型仪器来治疗癌症的技术。它发射的质子射线厚度很薄,精度误差小于1毫米,这一长度和铅笔的笔尖相当。这一技术可以非常精确地打击癌细胞,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传统放射性治疗手段中经常出现的对周边组织的损伤。
不幸的是,每一台质子治疗仪都需要用到一台加速质子的粒子回旋加速器,这种加速器可以使质子达到一定的、对治疗有效的速度。回旋加速器是一个圆形的装置,它的占地面积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而且其造价超过了1亿美元。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仅仅建造了13台这样的设备,而等待接受质子治疗仪治疗的病人通常要排很长的队。
但是癌症病人的未来是光明的。新的诸如近红外激光的治疗技术有希望在治疗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患者的损伤,而且这一切都将变得更加便宜。有潜力的新技术可以在细胞级别上对癌细胞展开进攻,也许在大多数人还不了解质子治疗仪为何物时,新技术就将其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