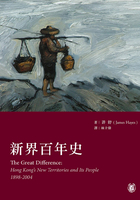
第四部分:鄉村文化
這是個不能不談的題目,因為它是農村生活的一部分,生動地反映了鄉民的信念與慣常做法。鄉村文化源自民族文化的大主體,而儒家倫理就是這個大主體的主要部分。鄉村文化着重家教和學校教育,陶鑄後代的模式與全中國其他地方大同小異。(76)
香港的鄉村文化一直鮮有人調查,直至近期情況才有所改變。但它有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物。(77)在1981年,科大衛談到他正在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的口述歷史計劃時說,他與同事和學生助手搜尋碑記和土地文件後,對村民有了更透徹的了解,這才「知道直至太平洋戰爭(1941-1945)前,新界素有非常豐富的地方文獻」。
這包括主要由村民自己撰寫的歌謠、詩詞,以及法律與禮儀文件。第二,許多人們所唱的歌謠,是靠口耳相傳的方式代代相傳,而從沒有記載下來。這些歌謠有的是新娘和她的家人在婚禮中唱;另有一些是在喪禮上唱;還有一批「山歌」,唱山歌是來自不同鄉村的年輕男女間的社交活動。和書寫文獻一樣,這些歌為我們生動地描繪鄉村生活的景象。(78)
從鄉村地區摭拾所得的文獻資料數目龐大,由此觀之,這該是各處均能找到的傳統。(79)上述石湖墟報德祠舉辦的詩文比賽也可看到,它現存的條文顯示,比賽內容是來自王朝時代的典籍。(80)
早在1930年代,香港學者宋學鵬就將錦田鄧氏的一些故事翻譯,刊登於《香港博物學家》(The Hong Kong Naturalist),指出有悠長的地方定居歷史的大宗族,對於這個重要文化領域的貢獻。(81)只出版了很短時間的中文刊物《新界週報》,在1960年代刊載了兩則來自屏山鄧氏的故事,它們都是與當地人高中科舉有關,正符合這個士人宗族的地位。其他沒有出版的屏山故事也陸續為人所知。(82)
對於新界建築感興趣的人,有同樣令人驚喜的事物在等待他們。對於這個本地文化的重要領域,也是要等到1970年代才更為人關注。香港大學建築系學生獲香港旅遊協會贊助做了一項調查,(83)香港政府新聞處把成果印製成書,十年後這本令人難以釋卷的書重印。(84)這本書主要論述大宗族的大型建築,以圍村、宗祠、書室、廟宇、塔和民居為重點,拍攝了大量石雕、陶塑、木雕和灰塑裝飾等民間建築的特色。儘管許多已因疏於修葺和拆卸而消失,但稍為遜色的同類事物,在新界其他古老鄉村仍可找到,令我們對1898年的鄉村景象有清晰了解。
那個時代瀰漫於鄉村社會的精神是毋庸置疑的。夏思義寫過一篇關於文學傳承的論文,探討當時鄉村學校校長許永慶(1839-1921)所寫的詩,指出它們「流露的氣息是滿懷自信、繫念社群和從容自主,這些似乎是上個世紀本地鄉村的特色」。我在更早期利用不同材料所做的另一項研究,也得出完全相同的結論。(85)
無論如何,風水也是鄉村文化的一部分:不只因為風水在歷史和傳說中是重要元素(如上文所見),還因為它是村民根深柢固的觀念。一如在1960年代一位大嶼山鄉村父老對我說:「對我們鄧氏族人來說,風水是頭等大事。」對於個人來說,根據出生年、月、日、時而定的八字同樣重要,婚嫁過大禮和迎親均須合八字,以占算良辰吉日,避免沖刑,用八字排命盤,可以得知所有人事的結果。(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