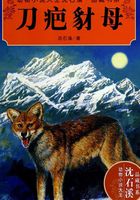
第6章 刀疤豺母(6)
刀疤豺母和它的臣民们,世世代代居住在尕玛尔草原,它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殖,这块土地滋养了它们,它们也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快乐与烦恼。豺是一种有领地意识的动物,同其他依附在大地上的生命一样,热土难舍,眷恋自己的故乡。如今,在人类的倾轧与威逼下,它们被迫离乡背井,逃离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茫茫雪山,漫漫旅途,前程未卜,大千世界,哪里是家?偌大的地球,竟容不下一窝金背豺!它们哭泣,它们哀叹,它们有理由向人类怒吼,有理由向苍天发出严厉的责问。
在豺群呦呦(左口右欧)(左口右欧)的啸叫声中,我依稀分辨出一个苍老的声音,叫得特别哀婉特别凄惨,我相信这是刀疤豺母发出的叫声。这缕不太和谐的苍老的声音,像是在乞求饶恕和原宥,像是在呼唤理解和宽容。我了解刀疤豺母,这是一只饱经风霜的老母豺,宽厚仁慈,与人为善。它在翻越雪山垭口的最后时刻,仍抱着一丝幻想,希望人类能丢掉对豺的成见,改变主意,同意它和它的臣民们继续留在尕玛尔草原生活。
谁愿意流落异乡为异客呢?
当豺群在山脊线上停止啸叫时,卡扎寨牧民从各家的毡房里取来了猎枪、铜鼓、响弩和牛角号,有的朝天放枪,有的擂响铜鼓,有的发射响弩,有的吹奏牛角号。牛厩里的牦牛哞哞直吼,羊圈里的山羊咩咩叫唤,马扬鬃嘶鸣,狗狂吠咆哮,整个寨子喧嚣得快要沸腾了。
我晓得,这绝非友好的欢送。这是声势浩大的驱赶、毫不留情的撵逐,含有用武力押解出境的性质。
我的视线一直凝聚在刀疤豺母身上,我看见,它好像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那剪影一下子缩小了许多,不难猜想,是泄气了,绝望了,也许是难过得趴在地上了。过了约数分钟,它的剪影又慢慢升高,再次站了起来,朝雪山垭口走去。
豺群跟随着刀疤豺母朝雪山垭口移动。
白茫茫的雪坡上,几十个黑影在蠕动。高原缺氧,积雪太厚,登高爬坡,它们跋涉得极其缓慢,步履沉重而又艰难,远远望去,就像蜗牛在爬一样。枪声、鼓声、弩箭声、狗吠声和牛角号声持续不断地响着,不让它们回头,催促它们快走,断绝它们退路,无情地粉碎它们最后一丝侥幸心理。
半个小时后,豺群消失在风雪凄迷的雪山垭口。
日曲卡雪峰北边这道垭口,是出入尕玛尔草原的门户。对豺群来说,走出雪山垭口,等于被扫地出门。雪山垭口终年积雪,一年四季中秋冬春三季大雪纷飞,两边陡峭的山峰上常发生雪崩,肆虐的暴风雪像把加密的巨锁锁住了这道门户,连最耐寒的雪豹都无法穿越,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只有夏末才能通行。毫不夸张地说,垭口难行,难于上青天。豺群这一去,怕是永远也回不来了。
村民们欣喜如狂,有的放起鞭炮,有的抬出酒坛,饮酒作乐,举杯相庆。
我知道,保持生态平衡,物种的多样性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物种消失,生态很有可能因此出现紊乱。大自然存在着一条环环相扣的生物圈,就像一根链条一样,一个环节断了,其他环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危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命系统。生态平衡被粗暴打破,是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啊。我高兴不起来,心里沉甸甸的,躲进藏式毡房,暗暗叹气。
强巴端着满满一铜碗青稞酒冲进毡房来,喜气洋洋地冲着我嚷道:“没有豺狼的日子,就是牧民的盛大节日。来,为恶豺永远从尕玛尔草原消失,干了这一杯!”
我摇摇头,没去接他的酒碗:“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问你,藏语里尕玛尔草原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有豺狗出没的草原。”强巴答道。
“这就对了,”我说,“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人类、金背豺和其他动物共同生活的地方,你们现在赶走了金背豺,打破了生态平衡,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你别老摆出一副动物学家的嘴脸来教训人吓唬人。”强巴不悦地说,“没了豺狗,只会是草更绿羊更肥牛更壮牧民更富裕。这喜庆的酒你不肯喝算了,你跟我们牧民不是一条心。”
强巴说着,将铜碗里的酒泼在地上,气嘟嘟地跑了出去。
无论藏民还是汉人,牧民的性格都憨厚耿直,说话直来直去,冲撞你没商量。我对强巴唐突的举动毫不介意,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金背豺搬迁后,尕玛尔草原气象更新,草更绿羊更肥牛更壮牧民更富裕,我心甘情愿受他的责骂。
唉,只怕是适得其反啊!
十
金背豺搬迁后,一段时间,尕玛尔草原果然如强巴所预言的那样,一派生机盎然。金背豺一走,草原上除了鹞鹰就没有其他食肉猛兽了,而鹞鹰除了偶尔捕食刚出生的羊羔外,是无法猎杀牦牛和成年羊的。羊群不再需要牧羊人照看,牧羊狗都下岗待业了,牦牛自由自在地溜达,哪儿牧草丰盛往哪儿拱,不用担心会遭遇不测。天敌逃遁,危机解除,生存压力顿释,牛羊心宽体胖,羊儿肥得轻轻一掐就能从羊屁股上掐出油来,牦牛壮得油光水滑,皮囊被绷得鼓鼓囊囊。卡扎寨一位李姓汉族牧民家一只母羊产下双胞羊羔,这在尕玛尔草原是破天荒的大喜事,全寨男女老少都上门去祝贺。另一位名叫亚钟的藏族牧民养的一头牦牛体重超过八百公斤,被评为全州的牦牛冠军,州长亲自给亚钟戴大红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最让卡扎寨牧民欢欣鼓舞的还是红毛雪兔数量日益增多。过去金背豺在的时候,虽然也有红毛雪兔,但数量有限,偶尔才能见到。牧民带着训练有素的猎狗到草原狩猎,辛苦大半天,也不一定就能逮到一只红毛雪兔。金背豺搬迁后,仅仅过了三个多月,过去难得一见的红毛雪兔便成了尕玛尔草原一道亮丽风景。清晨来到草原,扯一把草丝,绾成一只草帽,戴在头上,稍事伪装后静静地蹲下来,几分钟后,便能看到碧绿的草丛中红色的身影精灵般地闪耀跳动。牧民带着猎狗到草原狩猎,半天时辰,枪法再差劲的猎手,再愚钝笨拙的猎狗,也不会空手而归,枪尖上总能挑着一两只红毛雪兔神气活现地回家来。红毛雪兔虽不及牛羊肉鲜美,但属于野物,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不仅兔肉可以食用,兔皮也能晾干硝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虽不如水獭、冬狐、金猫等皮子那般贵重,一张兔皮值不了几个大钱,但换点油盐酱醋还是绰绰有余的。
卡扎寨有好几户藏族和汉族牧民,将羊群交给牧羊狗管理,让牦牛像野牛似的任其在草原游荡,腾出时间和精力来,专门捕猎红毛雪兔,当作一项贴补家用的副业,日子倒也过得逍遥。
强巴不无讽刺地对我说:“你说恶豺走了会破坏生态平衡,可事实上我们牧民的日子越过越滋润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确实无话可说,但愿我的预言永远不会变成现实。
然而,科学终归是科学,科学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该发生的事情迟早是会发生的。
四个多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红毛雪兔的数量迅速增长。过去走进尕玛尔草原,在红毛雪兔活动最频繁的清晨,要用草丝编帽戴在头上伪装起来,蹲在草丛里纹丝不动大气不喘静静等待仔细分辨,才能看到红毛雪兔的身影。如今,任何时候踏进草原,不必费心伪装,唱着歌信步走去,就算是深度近视眼也立刻就能发现红毛雪兔在绿草丛中晃动。过去猎人牵着猎狗在草原奔波老半天,靠运气才能逮着红毛雪兔。如今不需要猎人亲自出马,只消将猎狗吆喝进草原,一两个小时后,猎狗就会叼回一只半死不活的红毛雪兔。某日早晨,几个村民到尕玛尔草原寻找走散的牦牛,毫无目标地对准一片灌木丛乱放了一排枪,竟然有两只红毛雪兔撞在了枪口上。少年背着古老的金竹弩,到草原玩耍,也能用弩箭射倒几只红毛雪兔带回家。
面对红毛雪兔数量迅猛发展的势头,开始村民并没觉得是一种灾难的预兆。恰恰相反,许多人还认为是件天大的好事,可以靠红毛雪兔发财致富了。我建议在红毛雪兔还没泛滥成灾时,及早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遏制红毛雪兔急剧膨胀的数量。强巴瞪大一双惊愕的眼睛,就像在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说:“你是怕钱多了会咬手吗?你是存心不想让我们牧民过上富裕的好日子吗?红毛雪兔多了,是件大好事嘛。我们可以组织专业狩猎队,专门捕猎红毛雪兔。我们可以办一家肉食加工厂,把新鲜兔肉腌制成腊肉,运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去出售,我们还可以办一个皮毛加工厂,将兔皮精加工,制成美丽的高附加值的裘皮时装,与外贸公司联系,出口到国外去,赚大把大把的外汇。总之,红毛雪兔多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我耐心地开导他:“任何事情都有个度。一般来说,红毛雪兔数量多一些,是件好事,能给卡扎寨牧民带来额外收入,但也不是越多越好,超出了极限,好事就会变成坏事,就会带来预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我好歹是个动物学家,专门干这一行的,这方面的书读了近二十年,你应当相信我的话。我不会平白无故来害你们的。”
“红毛雪兔皮子可以剥下来卖钱,兔肉可以食用,兔骨碾碎成骨粉可以做鸡鸭饲料。你说,这红毛雪兔多了有何不好?”
“红毛雪兔属于啮齿类动物,繁殖率极高,一年能生三胎,每胎可产六至十二只,幼兔长到半年后,又可交配繁殖,从理论上说,一对成年红毛雪兔两年内可繁殖到一万多只。凡啮齿类动物,一生都在不断地长牙齿,要靠啃咬来磨短两颗门齿,因此会不停地啃咬草根树皮,对植被的破坏极大。要是不加限制任其发展,极有可能会把尕玛尔草原糟蹋光。还有,红毛雪兔大量暴尸野外的话,很有可能会流行可怕的瘟疫……”
“行了,你不用说这些话来吓唬我。”强巴不满地打断我的话,“我们卡扎寨牧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从来没听说过尕玛尔草原会被一群兔子吃光。嘻嘻,你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你说你读过二十年书,哦,你总该记得这两句古诗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尕玛尔草原的草从来没有枯竭的时候,养得活再多的牛群和羊群。有好几次,眼瞅着冬季的荒火把草原烧得光秃秃,一场春雨,草原一夜之间又变得一片葱绿。尕玛尔草原是天神赐给我们牧民的聚宝盆,没有谁能够糟蹋她破坏她,更不用说小小的红毛雪兔了。”
唉,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我无能为力了。
又过了两个多月,红毛雪兔呈几何级数量增长,滚雪球般壮大,很快发展到令村民担忧的程度。
我见过尕玛尔草原冬天的景色,牧草一片金黄,在一望无际的金色的草海里,镶嵌着一株株一丛丛苍绿的云杉树,点缀着一片片洁白的薄雪,间或有星星点点艳红的狼毒花,色彩绚丽,美不胜收。可眼下的尕玛尔草原,金黄的牧草被无数兔牙连根啃断,变得枯黄,云杉树离地一公尺高的树干上,树皮被兔牙啃剥干净,难看得就像一群下肢已经溃烂的麻风病人。正值冬季,牧草进入蛰伏期,停止生长,红毛雪兔像个庞大的食草军团,还在不停地吃呀吃,冬季才过了一半,差不多把大半个尕玛尔草原像剃光头一样吃得光秃秃的,像患牛皮癣一样露出一大片一大片黑色的泥土。每当落日黄昏,饥饿的红毛雪兔从地缝和洞穴中拥出来,成千上万,在牧草间蚕食蠕动,形成触目惊心的红色恐怖。灾难已露出端倪,再这样发展下去,过完这个冬天,尕玛尔草原就有可能会变成一片不毛之地。
卡扎寨十六岁以上的男子个个摩拳擦掌,要求组织狩猎队,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捕猎红毛雪兔的群众运动。冬天是农闲季节,青壮劳力反正闲在家里没多少事情可干,打猎是最好的消遣。消灭那些红毛雪兔,既保护了尕玛尔草原的牧草资源,保护了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又是一项有利可图的副业,何乐而不为呢?卡扎寨所有的狗,不论土狗洋狗藏獒牧羊犬猎狐犬公狗母狗大狗小狗胖狗瘦狗老狗少狗黑狗白狗黄狗花狗癞皮狗,也都全体出动,大呼小叫地跟着主人到尕玛尔草原捕猎红毛雪兔。
狩猎队早出晚归,有时天晚了,干脆就烧堆篝火住在草原上。狗也挺卖力气,见到红毛雪兔的影子就穷追猛撵,累得口吐白沫也在所不惜,凶猛的狗吠声和刺耳的枪声从早响到晚,整个尕玛尔草原变得像座血腥味很浓的巨大的屠宰场。
强巴亲自出马,担任狩猎队长。这家伙剽悍英武,有百步穿杨的功夫,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神枪手,这方面还挺有谋略,将狩猎队分为四个小组,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扫荡,地毯式搜索,全方位围剿。然而,战绩却并不理想,辛苦一天,也就捕捉到几十只红毛雪兔。
尕玛尔草原在白垩纪时代是一片汪洋大海,新生代时由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挤压,发生地壳运动,沧海桑田,尕玛尔从大洋底冒出海平面,变成滇北高原一块平坦而又丰腴的草原,至今在土层里仍能找到各种贝壳化石。由于是海洋升高后形成的陆地,尕玛尔草原地表具有很明显的海洋地质特征,随处可见大片大片的珊瑚礁,有的隆出地面约一二十米高,有的陷落土层达几十公尺深,有的风化变形淤泥壅塞如断垣残壁,有的还保留旧时模样如蜂窝如蚁穴。珊瑚礁是由一种名叫珊瑚虫的动物尸骸堆积而成,形状怪异,布满大大小小的气孔、洞穴和窟窿,孔连孔,洞通洞,穴套穴,窟窿穿窟窿。